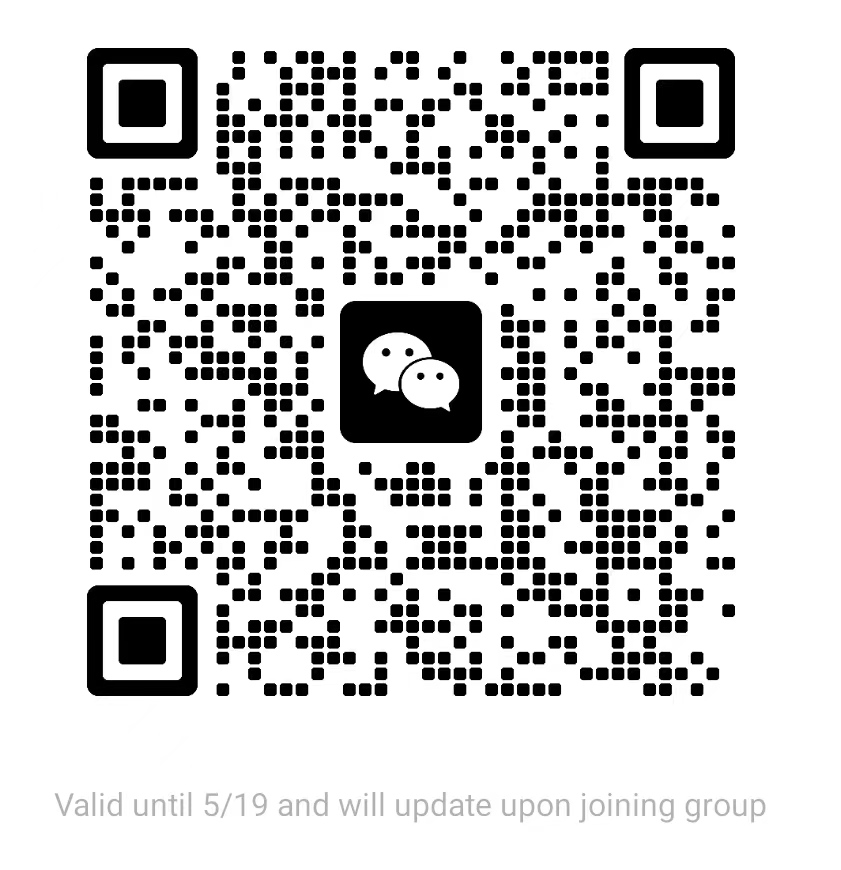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 杨奎松 >
- 讨论
附: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生发展情况。但由于年代湮远,文字档案甚少,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至今尚不十分清晰。这里,笔者根据所接触到的史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几个史实问题作些考察,希望能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1.中国最初有几家“共产党”?
通常,我们在一般史书上所能了解到的早期“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只有一家,即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个共产党。但对于专门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来说,人们实际上早就知道,在1920—1922年这段时间里,至少还出现过两个相对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即1922年在四川出现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和在法国建立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只是人们似乎还搞不清前者的确切名称和具体宗旨[1],同时有资料证明后者不论成立前或成立后,都同陈独秀等保持有密切联系。[2]最近,薛衔天先生的文章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早产的共产党,即1920年产生于俄国境内的“中华共产党”的情况。[3]于是,我们知道,至少在1920年6月,以旅俄华工及华侨为基础的联共(布)华人党员,也曾经在联共(布)党的帮助下,在苏俄组织过一个“中华共产党”。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几个我们过去很少知道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产生或存在过。已知1920年初在山东曾经诞生过一个“中国社会党”[4],辛亥年间就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这时也曾宣布他组织过一个社会党。即使除去那个默默无闻且不知所终的“中国社会党”,和江亢虎有名无实的社会党不计,可以肯定的是,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和有文字记载的,也至少还有四家“共产党”。它们就是:(1)四川重庆“共产党”;(2)北京“中国共产党”;(3)北京“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4)“无政府共产主义党”。
重庆的“共产党”是“由少数教师、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建立的”[5]。根据他们当年提供给共产国际的一份书面报告的内容,这些教师似乎早就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并且对一些大学生和工人发生了影响,其具体形成时间虽颇难判定,但可知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共同“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个重庆的“共产党”。[6]有关这个情况,我们目前还只知道它在1920年下半年的时候有过大约100个正式的或候补的成员,其内部曾有过书记处以及宣传、出版、财政之类的机构设置,除了重庆以外,它还在四川其他四个地方设立过分支机构,并曾计划于1921年正式开办自己的印刷所,以便更广泛地向学生和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7]除此之外,我们还不了解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8]
不过,看起来这确是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明确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将来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武器”,由于资本家和军阀试图在中国推行作为“维护少数资本家的权利而危害多数人,危害无产阶级的原则和手段”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产阶级只能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去与之对抗。他们并且表示坚信,在中国必须用苏俄式的红军来取代现在的军阀武装,同时必须将一切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9]
关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多半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小组织。有关这个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细节资料还几乎无从知晓。目前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可以认定的只有一点,即有一个名叫姚作宾(1891—1951)的人通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的介绍,曾经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过有关承认和支持该组织的问题。但据台湾学者王觉源考评,姚作宾、黄介民(1883—1956)等于1921年9月所成立的这一组织,在中国又取名为“大同党”,并没有叫“共产党”。[10]若王觉源这一考证成立,那么,可以相信这个组织并没有多少马克思或列宁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真实成分。其向共产国际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多半也只是为了求得国际上的帮助而已。[11]
在这几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中,最引人注目且有充分证据证明确有历史影响及活动的,还是“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就是北京当时著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其机关刊物《今日》杂志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其领导人为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投机官僚”[12]胡鄂公(字南湖)。据该会同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称,该组织正式成立于1922年2月16日,会上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为胡南湖,正式会员11008人,包括大中学生、工人、士兵、老师、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遍布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9个省市12个地区,总共有12个分支机构。其中央机关设于北京。报告称,他们已分别在京、津、晋、鄂、湘、川、赣等地,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山西、汉口等地开办了工人夜校,在四川组织有士兵俱乐部,在北京、天津、山西、四川等地出版有自己的宣传刊物。报告说,该组织“当前任务是参加工人运动,为改善劳动者的处境而斗争,以此来促使他们觉悟和团结”,使之能够投身于革命。他们的主张是:“革命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一旦推翻军阀之后,我们就立即向资产阶级宣战”,以便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国”。[13]这里可以判断的一点是,“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中的人员数字及其活动统计等,多半并不可信。
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目前尚无多少文字档案可供深入考察,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小团体,该组织的前身应该是1914年广州的刘师复创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组织是1919年左右成立起来的,最初名叫“无政府主义互助团”,后改名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领导人为北京大学的黄凌霜、陈德荣等,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漳州等几处成员加起来不过40人左右。其具体活动,在早已公开的北洋政府密探关谦的密报中多有记载。[14]
以上情况说明,由陈独秀等人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中国第一个,也不是中国最后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尽管上述组织或其成员并非真的都那么了解或信仰共产主义,甚或多半并不真的知道马克思或列宁的共产主义为何物,但考虑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同样存在着这种一知半解的情况,似乎很难将其一概否定,并且不承认它们的历史存在。
承认这一事实,才有助于看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2.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相互关系
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进行准确的描述。我们知道,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同吴玉章谈到过的那个四川的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直到1924年,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在四川开始活动之际,那个“中国YC团”不仅仍旧存在,而且同社会主义青年团似乎还有着合作关系。[15]至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同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的关系,初时不仅极力把后者引为同志[16],而且与其在组织上一度相互混合,一直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与其合作,而莫斯科的政策也根本改变为止。
可是,对于其他类似的组织,情况却不大相同了。就目前所知,在苏俄境内成立的“中华共产党”同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虽然有资料表明,在1920年前后,他们曾经先后派遣过大批华工以及华侨回国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7],但是,无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标榜共产主义的团体,显然都不是他们组织起来的。不仅如此,这个曾代表过中国共产主义者出席过两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18],在国内共产主义组织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之后,竟很快消失。其组织中的重要成员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转入国内的共产党来了。
试图把中国倾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的,是联共(布)党以及共产国际。1920—1921年,联共(布)党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在上海召集过有中、朝、日等国革命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以鼓动远东各国革命者建立社会主义组织,乃至于共产主义组织,进行相应的宣传。其中中国方面的代表不仅有陈独秀,也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黄凌霜等。[19]在广州,苏俄代表甚至还努力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组织在同一个团体中。[20]在北京,他们则同意为任何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提供帮助。
看来在1921年前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形还不十分清楚,它显然乐于更广泛地接纳中国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来访者。为此,它不仅接受了俄共远东局推荐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张太雷、俞秀松等,而且还不顾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反对,批准江亢虎享有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并且郑重其事地同姚作宾就共产国际对其组织的支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胡南湖派去的彭岳狱、彭今夷两位代表所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研究。
同时承认上述组织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在共产国际或许只是设法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策略。然而,在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看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在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与会者就明确主张作出规定,对于其他一切党派,只能“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甚至必须“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21]他们显然确信,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他党派充其量都只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为此,张太雷和俞秀松曾经接连四次向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和抗议,反对他们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指出江亢虎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说“中国青年对他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给他以代表资格,“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便于他“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22]同时,他们对姚作宾自称“中国共产党代表”也表示愤慨,明确声称不承认共产国际“同他讨论并且决定的任何东西”,宣布姚本人早已“成为中国学生的卑鄙的叛徒”。[23]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确定的出席其“三大”的中国代表团名单[24]和以后的情况看,这种抗议多半是发生了效力的,因为事实上共产国际此后再也没有同江亢虎及姚作宾等发生关系,他们的所谓组织也很快销声匿迹或不复以共产党的名义存在了。
不过,并不是除了陈独秀的共产党以外,所有的试图独立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组织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所派赴莫斯科的四位代表[25]的命运及结果,目前还没有文献可以考证,但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情况至少明显地有所不同。该组织的代表在1922年赴莫斯科时固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却仍旧同共产国际代表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并独立存在了一年以上。在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准备联合国民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1922年夏天,他们甚至一度宣布陈独秀等已经“变节”[26],力图要取代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中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为此,两个组织间自然一度公开论战,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曾撰文斥责对方根本不了解“第三国际理论”,甚至宣称胡南湖“不过是光怪陆离的东方匿报投机官僚罢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还曾公开揭露了胡鄂公在北京政府及国会中的所谓政客“投机”活动。[27]但是,不久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劝说和推动之下,两方面又握手言和。“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很快就合并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胡南湖等亦得以一度转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28]
3.党的经费来源与生存发展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党关系之一斑。很明显,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后者主动所造成的,它确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产生容易,其生存和发展却必须要得到后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这是同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工业极为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都极其欠缺薄弱。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来同中国工人缺少联系,而且一向深受日本及英美社会思潮影响,很少同俄国共产主义者发生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纵有应时而生的所谓共产主义组织,只有在取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支持时,才能确保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稳固和发展。在这方面,过去人们一向对这种理论上和思想的需要谈得较多,而对于物质上的需要则谈得较少。有人甚至断言,当时的共产党人根本就拒绝这种帮助。[29]事实并非如此。
从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姚作宾、江亢虎、胡南湖等,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目的之一,都是希望获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帮助。而其组织之难于独立生存与发展,则同共产国际不能提供这种帮助不无关系。同样,早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这种需要也十分明显。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之前,陈独秀等人多半只能从教书、编辑以及写文章所获薪水和稿费中支取部分金钱,用于支持一两份同仁刊物。对于其他社会活动,即使视为有极大意义,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等,显然也无力给予更多的资助。而维经斯基等来后,随着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宣传、组织等项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其所需费用也远远超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而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则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项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不得不停止”[30],就连用于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10余元路费竟也拿不出来了。[31]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32]这时国内党员约170人左右,且多数尚有社会职业,故所费甚少,以“其他二千余元”为党员消费计,人平均尚不足13元,并且还可“自行募捐一千元”。但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其党员自筹款数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而已。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但是,随着党的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而经费来源却相应减少了。尽管中共“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33],实际自筹款数却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前八个月,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34]。由于自1923年起党的经费与工人运动的经费已经分开,由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分别提供,因此1923年用于党组织本身活动的费用明显增多。另外,党的经费增加同党的人数的增加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人数的增加却并不能使党的自筹款项在总经费中的比例有所加大。也就是说,党在经费上对共产国际的需要绝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当然,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总是有限度的,它所提供的党费不可能与党员人数的增加同比例地无限制地增长。这里,我们可以做一张简表来显示它们的关系:
由上表可知,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已远远跟不上党员增长的速度了。但是,这是不是说随着党员数量的增长,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少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尽管党员不断地增加,但共产党人自筹款项的数额仍旧十分之少。到1927年,其党费收入仍不足3000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就有近100万元之多。其自筹款项实际不足3%。
上面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期对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而且还十分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正是这诸多的需要迫使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种近乎依赖式的关系。真正改变这种关系,不仅需要政治上、理论上以及斗争经验上的日渐成熟,而且还必须在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并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这种依存关系就很难根本改变。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
[1] 吴玉章回忆该组织名称为“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查《杨闇公日记》,知其1922—1923年组织名称的英文缩写为“CY”,1924年4月改为“YC”。另见其机关刊物《赤心评论》第1期,知“YC”即“中国YC团”,至于此“中国YC团”中文全称为何,尚不得而知。
[2] 甚至在1922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里,已经认定这个在法国由张申府等人组织起来的小组为中共的下级组织了。
[3] 见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4] 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
[5]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6] 同上,引文中1920年或为1921年之误。
[7] 同上。
[8] 新近的研究可参见杨世元:《试析“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期;《“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四川党史》1998年第4期;李蓉:《对“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
[9]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10]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121页。
[11] 有关这个大同党的更具体的情况,如今可见黄介民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近代史资料》第12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田诚:《“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13]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1922年。
[14] 有关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及其组织活动的情况,也包括北京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的相关情况,如今可参见李丹阳等著:《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等。
[15] 参见《杨闇公日记》,第89页页下注。
[16] 类似的言论在《共产党》月刊上随处可见。
[17] 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8] 在1920年6月以前,该组织是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6月以后,相关文件中仍标注其为“中国工人党中央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47页。
[19] 参见《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共产党》,第40—42页;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1853—1922)》,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77—278页。
[20] 《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2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页。
[22]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等。
[23] 《俞秀松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8日。
[24] 在1921年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上,正式承认的中国代表只有张太雷和俞秀松,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余客人名单里还有瞿秋白等,但无论是代表还是客人名单中均无江亢虎等人了。
[25] “四川四人”应为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26] 《今日》第2卷第4号,1922年11月。
[27] 田诚:《“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28]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会议曾专门提到胡鄂公等“今日”派的党籍问题,它表明胡等至少在1923年10月以前已经转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4页。
[29] 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1953年8—9月。
[30] 《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3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
[3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页。
[33]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98页。
[34]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