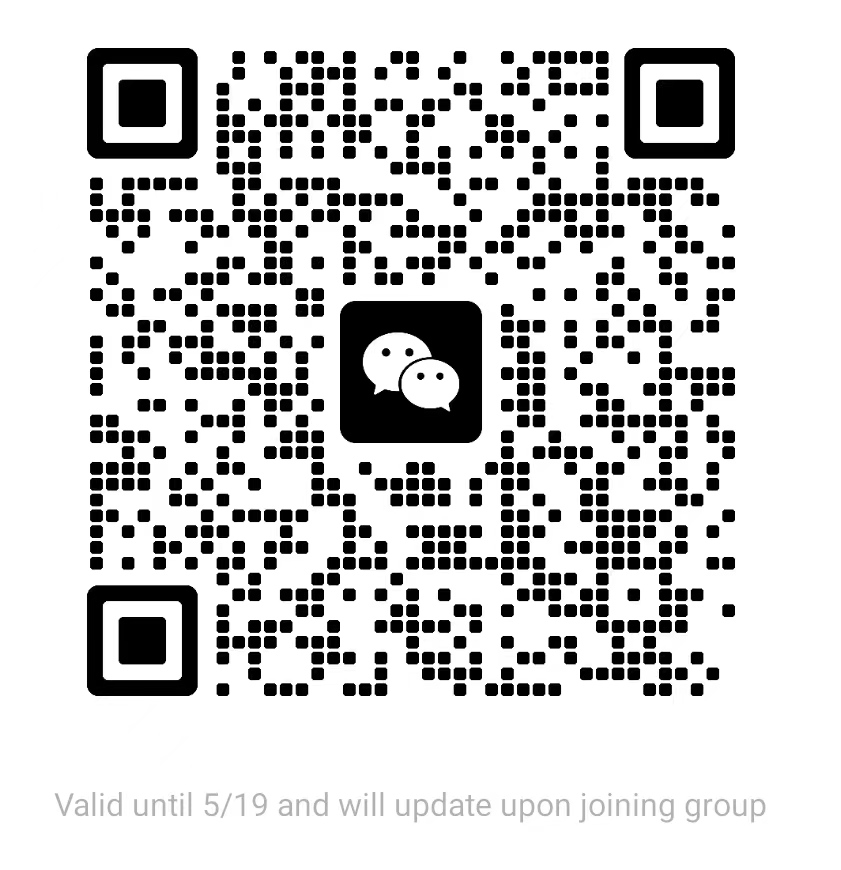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一册 >
- 第五章 神话的操演与破译 >
- 一、女娲补天:石头神话(贾宝玉)
(四)神瑛侍者
除石头神话之外,第一回有关贾宝玉的神话还有“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发生一段灌溉还泪的故事,是为“木石前盟”。
就小说叙事的整体结构而言,神瑛侍者势必是畸零玉石的另一化身。当此一畸零于天外的玉石欲下凡历劫之前,曾以自由之身至警幻仙子处游玩,此时其身份一变而为神瑛侍者,如此始得以甘露之水对林黛玉之前身的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最后才在警幻仙子前“挂了号”,由一僧一道引领至凡间受享繁华欢乐,并连带地引发绛珠仙草的入世以还泪偿恩,展开人间的另一段情缘。换言之,玉石幻形入世的过程里还有一个步骤,那便是以“神瑛侍者”为中介,其实也更透露石玉一体的内在消息:其中所谓的“神”字作为对立于“俗”界的意义自不待言,而所谓的“瑛”字就殊堪玩味了:《说文解字》对瑛字的解释是“玉光也”,《玉篇》则谓:“瑛,美石,似玉;水精谓之玉瑛也。”可见瑛与玉根本就出于同一个范畴,彼此十分近似,而且可以连“玉瑛”二字为一词,作为水晶之别称,则尚在神界的层次时,石头已非素朴之野物,而是经过锻炼、美质已具的玉石了。就此,可以再度证明女娲补天所遗之石确然为玉石,与入世后的通灵宝玉一以贯之。
只是,对于许多读者而言,补天弃石与贾宝玉、神瑛侍者的关系似乎很难等同为一。例如说,既然石头在听了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如此之粗蠢笨重而“不能见礼”,又如何可能是那一位游逛到西方灵河岸上,对干枯濒危的绛珠仙草“日以甘露灌溉”的赤瑕宫神瑛侍者?而此石化为美玉之后,是被含衔于宝玉口内落世的,玉石似乎又与贾宝玉分别为两个不同的个体。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科学化厘清的问题。然而,若把宝玉与玉石、神瑛区分为三,或个别地两两等同(如宝玉等于玉石而不等于神瑛、宝玉等于神瑛而不等于玉石),而非三者合一,却是万万不可,因为从整体的叙事结构而言,他们必须是同一的。唯有畸零玉石与神瑛侍者都是贾宝玉,才能与入世后的种种故事相符;更何况,人与玉石的合一可以有许多形式,不只是机械式的彼此等同,而可以是1+1=1,且1+1的组合方式可以有许多形态,而综摄于贾宝玉的整体人格内涵与个人命运上。就此,应该仔细思考的是,绛珠仙草受恩于神瑛侍者,故欲以眼泪还他,而入世后的苦恋对象为贾宝玉,因此第五回《红楼梦曲》的终身误一阕说的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第三十六回宝玉梦中喊骂的也是:“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足证神瑛侍者与贾宝玉是二合一的;再看第二十五回中,宝玉为马道婆的魔法所祟,已奄奄一息,就在生死一线之际,一僧一道及时赶来救治,要贾政将那块通灵宝玉取出来:
那僧道:“长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们持颂持颂,只怕就好了。”贾政听说,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接了过来,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
天不拘兮地不羁,
心头无喜亦无悲;
却因锻炼通灵后,
便向人间觅是非。
可叹你今日这番经历:
粉渍脂痕污宝光,
绮栊昼夜困鸳鸯。
沉酣一梦终须醒,
冤孽偿清好散场!
念毕,又摩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槛。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使阴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说着回头便走了。
如果宝玉不等于玉石,则僧道来拯救玉石有何意义?被作祟待毙的可是宝玉。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救宝玉,却持颂作法于通灵玉石,岂非更证明补天弃石与贾宝玉二者为一?果然“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的,是玉石也是宝玉,而玉石的恢复灵明同时也就是宝玉的起死回生,玉石可以说是宝玉的灵性或曰灵魂,甚至是生命本源。所以,会认为宝玉与玉石、神瑛并非一人的,都是执着于机械化的认知方式,忽略了“同一性”在人文世界与文学创作里具有多种可能的形式。
因此毋宁说,作者是根据入世后的种种叙事需要,也就是对贾府而言是人生价值上的无才补天、对林黛玉而言是爱情上的苦恋还泪,才后设地为之创造神话论述,分别给予一种先天命定的解释,因此他并不是在统一的构想下进行一个系统神话,也不在乎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符合科学的一致性;或者应该说,这两个神话之间以一种神秘的连结而通贯为一,其统一性或一致性不是以现代的物理机械式思维所建立的。因此,最近有学者甚至主张:“实际上,作者写了六位一体:石头、通灵玉、石书、神瑛、贾宝玉、作者。这些意象、幻相、物相六位一体,有共性,有个性,有相通相似内在联系,又各有区别。作者还写了一些意象、幻想、物相及事情加强六者之间的联系,如:悼红轩、赤瑕宫、绛芸轩、怡红院,并在通部书把石、玉、瑛的品格精神在宝玉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最后,石头复还本质,复归山下,身上‘编述历历’,是石头‘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作者带有自传色彩的书)。所以说,石头是投胎,起到了贯串始终的重要作用。”[37]当然,其中把作者与小说人物相等同,仍是可商的,请参本书第二章的说明;而除此之外,视石头、通灵玉、石书、神瑛、贾宝玉为五位一体,确是合乎整体叙事架构的认知。
[1] 见尹慧珉:《近年英美〈红楼梦〉论者评介》,《红楼梦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476。文中称“普拉克斯”,为Plaks的直接音译。
[2] 〔德〕埃利希·诺伊曼著,李以洪译:《大母神——一个原型的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3]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页172。
[4]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石头的生命循环与悲剧指归》,页178—191。
[5] (晋)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大荒西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88—389。
[6] 参钱中文主编,参李兆林等译:《巴赫金全集》第6卷《弗朗索瓦·拉柏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38。
[7] 〔美〕坎贝尔著,朱侃如译:《神话》(台北:立绪文化公司,1995),页74—75。
[8]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5。
[9] 〔英〕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Miranda Bruce-Mitford)等著,周继岚译:《符号与象征》(北京:三联书店,2010),页67。
[10] 〔美〕马丽加·金芭塔丝著,叶舒宪等译:《活着的女神》,页173。
[11] 参(晋)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大荒西经》,页389。
[12] 徐征等编:《全元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卷,页19。
[13] (唐)王冰次注:《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20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页48。
[14] 王孝廉:《石头的古代信仰与神话传说》,《中国的神话与传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页41。
[15] 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页313—316。
[16]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著,杨素娥译,胡国桢校:《圣与俗——宗教的本质》(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页101。
[17] 第八回夹批。
[18] 详参张苹:《从美石到礼玉——史前玉器的符号象征系统与礼仪文化进程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页93—94。
[19]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95),卷63,页1031。
[20] 同上书,卷30,页563—564。
[21] 详参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52—153。
[22] 见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页192。
[23]Carl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 of C. G. Ju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ume 9. Part 5, p. 235. 引自杨瑞:《〈聊斋志异〉中的母亲原型》,《文史哲》1997年第1期,页90。
[24] 依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父权制的性别和社会文化秩序,以菲勒斯(phallus)为中心,受父亲的法律(The Law of the Father)的支配。参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页115。
[25] (清)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89。
[26] 脂砚斋并认为“以此命名恰极”,见第一回眉批。
[27] 参〔美〕亚伦·强森(Allen G. Johnson)著,成令方等译:《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与承诺》(台北:群学出版社,2003),页101—110。
[28]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9] 如苏轼《儋耳山》的“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辛弃疾《归朝欢》的“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头闲处”,参刘上生:《走近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147。自宋玉《九辩》之后,陆续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等,篇名尤其显豁其义。
[30] 参朱淡文:《红楼梦研究》(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1),页5—9。
[31] 第十二回眉批。
[32] 或可参考以下说法:“本宗,从经济的这个角度来看,只能指溯及好几代的时点之前,彼此有同居共财的男系的共同祖先,且已经依据兄弟均分的原则,分割家产的这个集团,才能叫本宗。亦即,所谓别居异财的本宗是,虽然依时间远近而有所差异,但都是指曾营同居共财的男系血亲以及该男系子孙的妻子们而言。从而,一般来说,本宗的亲疏,亦即服制的序列,不只是根据男系血缘的浓淡,而且也跟同居共财关系的解消(=行家产分割)的时点远近也相一致。”参见〔日〕高桥芳郎:《唐代以来的窃盗罪与亲属——罪责减轻的缘由》,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页207。
[33] 眉批第二十二回。
[34] 此点详参欧丽娟:《身份认同与性别越界——〈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新论》,《台大中文学报》第31期(2009年12月),页197—242。
[35] 〔西汉〕司马迁:《史记》(台北:鼎文书局,1993),页1344。
[36] 详参李桂奎:《论中国古代小说的“百年”时间构架及其叙事功能》,《求是学刊》第32卷第1期(2005年1月),页109—113。
[37] 参展静:《〈红楼梦〉两个神话的意义》,崔川荣、萧凤芝主编:《红楼梦研究辑刊(第一辑)》(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页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