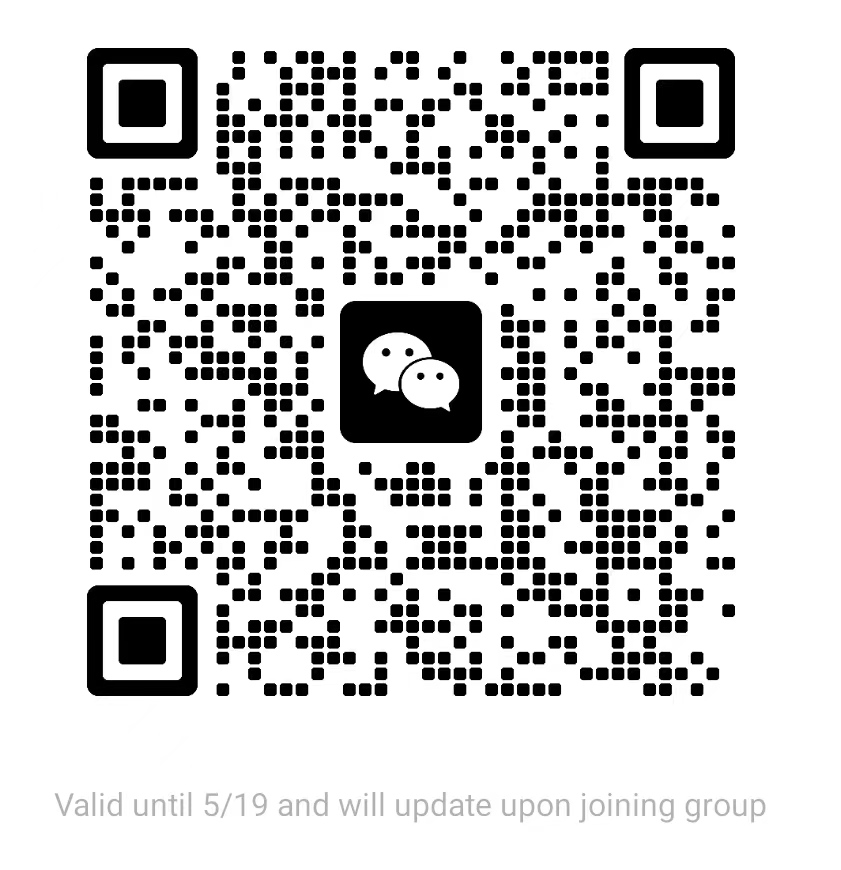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四册 >
- 第七章 红楼情榜
二、“以情为榜”的意义
(一)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
学者们纷纷注意到,在小说中将重要人物作一总集合,形成一张榜单,透过排列的顺序与注解进行评价,这并非曹雪芹的创始,而是来自传统章回小说的形式依据。《红楼梦》的情榜即类似于《水浒传》之石碣、《封神演义》第九十九回之封神榜、《水许后传》之座次表、《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之揭榜(幽榜),以及其后《镜花缘》第四十八回之无字碑(天榜)、《女仙外史》第八十二回之科榜,可以说,“‘榜’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不仅经历了从有实无名到名实相副的演化过程,而且经历了从天榜、神榜到幽榜、再到情榜、花榜的发展脉络”[1]。
首先,明清两朝的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在结构上多有一个“榜”的形式来品评人物、排列先后,或于开篇总领全书,或于中段承先启后,或于篇终压轴收结,如《封神演义》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名单的“封神榜”、《水浒传》设有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忠义榜”、《儒林外史》的“幽榜”、《镜花缘》的“无字碑”等。[2]这样的安排,“都有预示或收束全体人物的艺术功能,乃是谪凡模式的重要母题”,亦即谪凡神话模式中常用“榜”,以作为一种预示的母题,则“红楼情榜”乃作者用以揭示交代人物运数的结局。[3]不过,从残存的内容来看,警幻情榜并非用以交代人物的命运或结局,请参下文,“谪凡神话模式”则道中宝玉一干人等的仙界来历,由此进一步可知,这些章回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来自天庭的非常人,与世间庸碌的大众迥然不同,才能合理地演绎出曲折离奇的故事,令平凡的读者津津乐道。从这个角度而言,明清章回小说中的这几部“奇书”,不仅是书写形式上的出奇,也是人物本身的奇特。
此外,伊藤漱平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当时士大夫梦想的天界上的科举即“天榜”,对“情榜”的构想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4]试观宝玉的前身乃是女娲补天所炼造,其功能与目的本就是要完成“补天”所隐喻的济世大业,而对应到现实中,这只有出仕为宦才能达到。俱得补天的众石便是荣登天榜的佼佼者,那唯一无材补天的畸零石则是无用之徒,虽然逍遥自得、性灵满足,却无益于国家社会,因此,包括那“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第一回)的甄士隐,以及为曹雪芹点评小说的脂砚斋在内,都被称为废人:
•甄士隐本名“甄费”,谐音“真废”。(第一回眉批、夹批)
•脂砚斋自称“废人”。(第十八回批语)
这颗被弃的玉石既然补天无用,自然也进入了废人之列,但一味地“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本非自处之道,于是便如传统士人一样,宦途得志的时候是儒家,官场失意的时候就变成了道家,以无用为大用,并转向“以情为根”的青埂峰寻求出路,透过富贵场温柔乡中的“情痴情种”成为情榜上的状元。则从“天榜”到“情榜”,此中颇有弥补性的代偿意味。
(二)“女性”与“情”的品赏
当然,《红楼梦》是一阕女性的颂歌,以书写女性之种种丰采为主体,故作者前言即清楚表示其创作宗旨,乃是:“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因而这幅情榜势必以女性为主,太虚幻境中的每一簿册都以十二金钗为单位,乃理有固然。
据日本汉学家的看法,给予情榜的构想最大影响的,是当时流行的花案、花榜的风习,《红楼梦》旧名《金陵十二钗》,而十二钗常用来指称妓女,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曾称十二个名妓为“十二钗”,即是一证。[5]社会风习的熏染常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作用,曹雪芹对花榜也应该不会陌生,此一推测自属有据,不过应该特别厘清的是,名妓也许具有倾城的魅力,却身份低贱,与曹雪芹所主要书写的贵族女性判然有别。透过第二回贾雨村论“正邪两赋”一段所言: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
如此悬殊的成长环境与文化教养,让同一先天禀赋的正邪两赋者有了截然不同的人格内涵与生命形态,则两类不同出身的女性势必不可混为一谈,曹雪芹也断不能将闺秀才媛比拟于风尘女妓。尤其在曹雪芹所处的盛清时期,青楼的文化地位已然陡降,青楼与闺阁泾渭分明,不再处于文人文化的中心,闺秀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才德兼具的形象取而代之,成为这个时代所推崇的女性类型,则贾府中的金钗更不宜以花案、花榜上的妓女给予联想。这一点至关紧要,请参下文的说明。
其次,从“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之说,“情”字两见,而确实《红楼梦》全书写情入骨,动人肺腑,这部奇作也往往被视为以情为纲领的“情书”,所谓:
(《红楼梦》)情书也。……作是书者,盖生于情,发于情;钟于情,笃于情;深于情,恋于情;纵于情,困于情;癖于情,痴于情;乐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断于情;至极乎情,终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举一动,无在不用其情。此之谓情书。其情之中,欢洽之情太少,愁绪之情苦多。[6]
就此,周汝昌认为曹雪芹从冯梦龙的《情史》取得了启示,《情史》一名《情天宝鉴》,曹雪芹也曾把他自己的小说取名为《风月宝鉴》,题称接近,再加上《情史》的二十四个品类本身就构成了一张“情榜”,其细目包括:1.情贞;2.情缘;3.情私;4.情侠;5.情豪;6.情爱;7.情痴;8.情感;9.情幻;10.情灵;11.情化;12.情憾;13.情仇;14.情媒;15.情芽;16.情报;17.情累;18.情疑;19.情鬼;20.情妖;21.情通;22.情迹;23.情外;24.情秽。[7]以此对应于《红楼梦》的情书写,诚也约略可以看出类似之处。
只可惜,警幻情榜不仅残缺太甚,无以见其完整全貌与先后排序,人物品评更是零落殆尽,失去了探索人物性格的精确指引,只剩下宝玉、黛玉的两则评语,而且直接反映于情榜的排序上。
其实,就这幅榜单到底收录多少人物而言,无论是三十六人、六十人、一百零八人的各种说法,恐怕都是错误的,原因是榜单上并不只是收录太虚幻境中的各等簿册成员,凡以十二为单位的记数都遗漏了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贾宝玉,因此,榜单上应该是三十七人、六十一人或一百零九人。
宝玉不仅领衔居首,呼应了“绛洞花主”(第三十七回)、“总花神”(第七十八回)、“诸艳之贯”(第十七回回前总批)、“总一园之首”[8]乃至“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第四十六回脂批)的核心地位,并且在这幅以情为纲领的榜单上,他对情的体悟与展现,也最是动人心魄,情榜之首当之无愧。
情榜之首是宝玉,随后居次的则是黛玉,也只有这两个人物留下了评语,尤其是第十九回、第三十一回更是两者并置:
•按警幻情讲(榜),宝玉系“情不情”。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第八回眉批)
•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第十九回批语)
•“情不情。”(第二十三回评“恐怕脚步践踏了”一句)
•玉兄每“情不情”,况有情者乎?(第二十五回夹批)
•“撕扇子”是以不知情之物供姣嗔,不知情时(事)之人一笑,所谓“情不情”。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何颦儿为其所惑,故颦儿谓“情情”。(第三十一回回前总批)
可见在情榜上,“情不情”就是对宝玉的定论,其中,第一个“情”字是动词,指以真情、温情、深情对待一切人类以外的“不情”者,包括花草树木在内“无知无识”的无情物。此一超我的胸襟正是宝玉的前身神瑛侍者会去灌溉绛珠草的动因,并且幻形入世后,也会担心书房中画轴上的美人感到寂寞,于是前往望慰一番,此处的夹批也说“天生一段痴情,所谓‘情不情’也”(第十九回),都是点明宝玉的情广延于天地万物。基于这种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宽阔信念,宝玉便认定:
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第七十七回)
所以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外人看来不免觉得疯傻,其中却是深情无限,直如庄子的齐物胸怀,最为博大。
然而物极必反,情深、情博之至极往往走向无情,弘一大师的出家即为一典型例证,宝玉也踏上同一条道路。第三十五回写傅秋芳一段,有脂砚斋的长批云:
大抵诸色非情不生,非情不合。情之表见于爱,爱众则心无定象。心不定则诸幻丛生,诸魔蜂起,则汲汲乎流于无情。此宝玉之多情而不情之案,凡我同人其留意。
其实“多情而不情”既来自“爱众”也源于“情深”,其结果都不免走到“不情/无情”,此即所谓“情极之毒”,都与最终的悟彻出家有关。第二十一回袭人因宝玉屡劝不听,因而动气冷淡,宝玉也赌气不理,冷清自适,“便权当他们死了,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对此脂砚斋批云:
此意却好,但袭卿辈不应如此弃也。宝玉之情,今古无人可比固矣。然宝玉有情极之毒,亦世人莫忍为者,看至后半部,则洞明矣。此是宝王(第)三大病也。宝玉看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婢,岂能弃而而僧哉。玉一生偏僻处。
可见“情极之毒”意指舍弃凡人眷恋不舍的娇妻美妾,忍心撒手断离,飘然远去,对此,一般胶着于外相者将之目为无情,甚至加以苛责,但就宗教上所追求的解脱而言,则会赞叹“此是宝玉大智慧大力量处,别个不能,我也不能”(第二十一回批语)。从而,“情不情”也隐含着“情”以至“不情”的悟道轨迹,这时的“不情”就变成了动词,指“超越、断舍其情”之意。
在情榜上次于宝玉者,即为黛玉。黛玉的“情情”意指只对“有情物”有情,比起宝玉那包笼一切人与物在内的“情不情”,范围便狭小得多,因此当其钟情之时往往过分执著,而难免偏执之病。吊诡的是,“情情”的执著固然因更加集中而浓烈,但其结果却没有产生“不情”的“情极之毒”,以致黛玉终身沉沦于情之缠陷中,直到泪尽而逝,正提供了《楞严经》所说“爱河干枯,令汝解脱”[9]的具体范例,虽浪漫感人,却也发人深省。
关于情榜上的第三名,脂批中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但从脂砚斋一再提醒宝、黛、钗三人“鼎立”(第五回眉批)、“三人一体”(第二十八回眉批),以重要性而言,合理的推测应是宝钗,自无疑义。不过,基于扬黛抑钗的人物评价主流,读者对宝钗在情榜上的按语往往给予负面的推论,如张爱玲直接断言道:“签诗是‘任是无情也动人’,情榜上宝钗的评语内一定有‘无情’二字。”[10]但其实“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签诗完全没有“无情”的意思,何况“无情”的解释也不是只有常识上所以为的冷酷那一种,请参《大观红楼3》“薛宝钗论”。最重要的是,既然所有的材料都没有提供证据,吾人便毋须揣测附会,以免落入无稽之谈。
必须注意到,犹如第五回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所聆听的仙曲,其前奏清楚地说:
〔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对这些金玉般的红楼女子既怀念且悲悼,何尝有一丁点不满或讽刺的意味?参照宝钗曾经当面对平儿赞美道:“我们没事评论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第三十九回)正呼应了凤姐感叹说:“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第五十五回)这两段话其实可以普遍地用在小说中的诸多女性人物身上,金钗们各有其惊才绝艳的丰姿,而平儿尚且只是副册乃至又副册的女子,已经是百中不能选一,遑论正册之辈?与宝玉、黛玉鼎立的宝钗势必有其非凡之处,在“情”的范畴上,比起宝玉之博、黛玉之浓,宝钗应是“太上忘情”之透,自有俗人难测之奥义。
此外,小说家在回目上的用语,似乎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包括:第三十二回的“含耻辱情烈死金钏”、第六十六回的“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分别以“情烈”“耻情”概括金钏、尤三姐的自尽。作为情节的指引,对应的是当事人在特定状况下的心理情态,但能否直接等同于情榜上的人物评论,恐怕仍待商榷,从严格的标准而言,只能作为参考。
(三)“情”的道德原则
不仅如此,“情”的范围包罗甚广,层次复杂,如同其他的概念如自由、平等一样,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世俗甚至往往情、欲不分,干扰了情的真正面目与核心价值。因此,《红楼梦》对于情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没有标准的,也隐隐约约体现于幻境簿册与警幻情榜的排序上。
最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引子》中开篇所说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已经清楚区分了“情种”并不是落入皮肤滥淫的“风月情浓”,就此,张新之的儒家式评点十分令人玩味,所谓:
曰“谁为情种”,曰“都只为风月情浓”,见“情种”所以难得者,正为“风月情浓”者在在皆是耳。可见“情种”是一事,“风月情浓”又是一事。则真正“情种”当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设若不作此解,则“谁为”一起、“都只为”一承,岂不是大不通的语句?[11]
如此便从语法脉络与训诂角度,厘清了“情种”的意义不但与一般的“风月情浓”无关,甚至进一步证成了“礼度”与“情痴情种”的关系,这当然与道德标准有关。秦可卿之所以垫居正册之末,正是兼具了这一层的考虑在内。
同样的,关于幻境簿册与情榜的排序原则,除身份等级是明确的基本标准之外,评点家周春也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说道:
案婢女贱流,例入又副册,香菱以能诗超入副册,鸳鸯贞烈,竟进于十二钗矣。盖此书专言情,情欲肆则天理灭亡,以鸳鸯、秦可卿殿十二钗,所谓欲尽理来也。……乃全书之微旨,异于《金瓶梅》《玉娇梨》者在此,特拈出之。[12]
周春以“能诗”与否、“贞烈”与否的两个标准,解释香菱与鸳鸯之所在位置,此一说法虽未必完全正确,如香菱之所以进入副册,并非因为“能诗”的缘故,而是因为阶级向下流动所造成的身份暧昧,鸳鸯也没有跻身于“正十二钗”,因此必须保留;但所谓“此书专言情,情欲肆则天理灭亡”“欲尽理来”的看法,则与曹雪芹的情观相吻合。
从诞生《红楼梦》的特定时空与特定阶层而言,《红楼梦》中所追慕的闺阁女性截然不是晚明所追捧的青楼名妓,曹雪芹所弘扬的情也迥异于晚明名妓文化中的情。诚如高彦颐已说明的,名妓不仅在晚明的文学与道德伦理论述中占有核心地位,甚至在士人阶层的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3],曼素恩(Susan Mann)则进一步指出,盛清时期的妇女论述与晚明以“情”为重的论述大相径庭,在“家庭道德主义”(familistic moralism)的论述下,“18世纪中,高级妓院里的妇女,与闺阁里深居简出的妇女,她们所各自占据的世界,似乎彼此分隔得愈来愈远。……盛清在名妓的居处和闺秀所居住的闺阁之间标示出严格的分界线。虽然盛清名妓就像她们的晚明前辈一般,有时仍会写出精致的古典诗,并且就范围涵括艺术、文学与历史的话题进行交谈,但是,她们却不再占据士人文化的中心地位。相反地,在盛清时代,占据这个中心的聪慧妇女,正是闺秀本身……上流阶层的女性作者也获得了新的地位。”于是“闺阁”这个女性空间成为妇女才德典范的象征。[14]
《红楼梦》主要所写的,正是此一时代公侯富贵之家的闺秀群,礼法道德是她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在家庭环境中自幼耳濡目染的影响下,也成为她们心灵构造上的基本核心,其所谓情的性质与形态绝不能混淆于名妓的情,更迥别于一般庶民缺乏教育与德性概念之下的自由恋爱。从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代表人物身上,可以清楚显示他们即使各自的性格差异甚大,仍有一个共同的情感标准,那就是始终没有逾越礼教规范,却又丝毫没有减损其情的深度与纯度,为此,曹雪芹特别创造了一个用来超越痴情的“痴理”说,以展现“情理兼备”而“两尽其道”的最高境界。[15]
何况,姑且不论盛清时期上层精英阶级的特定文化观,就一般的普遍意义而言,正如哲学家所提问的:
如果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我们如何能够负有道德上的责任,以从事正确的选择,而避免沦入快乐与色欲的诱惑?而且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做的选择没有道德上的责任,那么我们将依照何种判准来评价或谴责一个人的品格或行为?[16]
以《红楼梦》来说,秦可卿身为综合宝钗、黛玉、香菱、凤姐之长的兼美人物,却以爬灰的乱伦悖德而青春丧命,岂能只因出于真情之故便加以肯定?非大家闺秀出身的尤氏姊妹若非双双改邪归正,为了真正心有所属的对象而非礼勿动,守贞节烈之表现不亚于名门闺秀,其原先浮浪无度的举止言行又如何能获得同情或宽容?丫鬟司棋与表哥潘又安的偷情导致大观园的抄检、自我的毁灭,果真可以用“情欲自主”给予赞扬?这些人或者因为某些病态的原因,或者因为没有受过教育,所不能明白的是,其实“情”并不只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感觉,更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并且产生了情之后,接下来的思考和作为才是赋予情以价值的关键阶段,而与人们的“选择”息息相关。
从本质上来说,情和自由、平等一样,都不是无限制的善事物,哲学家指出,“有不同种类的真,不同模型的善,不同意义的美。在自由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不仅具备了生来即拥有的根植于人性之内的自由,即天生自然的自由(natural freedom),还可以追求一种与智慧及伦理美德(道德美德,moral virtue)相联结的自由,可称之为后天得到的自由(acquires freedom),这两种自由都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减损与剥夺。而“选择”便来自人们的自由意志,亦即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去决定自己要成为何种人,并努力自我塑造:
我们的天生自然的自由存在于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它是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能够再选择我们已选择过的其他的自由。拥有这种自由,我们的行为才不会像其他动物的行为,受到对我们的发展有所影响的外在环境所本能地决定或完全制约。带有这种自由选择的内在能力,每一个人都能借着为自己决定将做或将成为什么,而创造性地改变自己的品格。我们有自由使自己成为我们所选择的。[17]
这里分析的是“自由”,却同样适用于对“情”的理解。人们不仅具备了生来即拥有的根植于人性之内的情,还可以追求一种与智慧及伦理美德(道德美德)相联结的情,而人们的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哪一种情,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改变自己的性格,决定自己成为何种人。所以,情的内涵与价值直接关联于一个人的品格,这也是警幻情榜上的情带有道德原则的原因。
固然一个虚构人物的艺术价值不在于褒贬,而在于他对读者所带来的启发性,并且每一个人都有其无奈与困境,因此未必都要给予道德上的评价,但是不能不思考的是,现代读者都受过良好教育,能进行各种阅读学习,却往往素朴地以“天生自然的情”进行人物褒贬,忽略了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情,亦即在其个人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与智慧及伦理美德(道德美德)相联结的情”,甚至情、欲混淆,岂非买椟还珠,甚至自我降格?
最可惜的是,一般人大多不知道自己拥有一种“每一个人都能借着为自己决定将做或将成为什么,而创造性地改变自己的品格”的自由,放弃了“使自己成为我们所选择的”这完全可以操之在我的机会,以至于流入本能与市俗,这就是曹雪芹要书写《红楼梦》的原因。如第八回脂砚斋所云:“作者是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借由秦可卿的案例悲叹于情之滥用、误导,被用来屏障种种悖德行径,以为只要有情便可为所欲为,以至于真情产生了变质与扭曲,成为私情、淫欲的掩护。
在个人主义式的自由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中,“感觉本能”被过分夸大,“情”的掩蔽愈烈,对曹雪芹所苦心刻画之情也误解更甚。既然情榜已然遗落,失去了参照的坐标,那么回到小说情节中仔细分析,透过理性的思考、正确的知识,由衷尊重盛清时代的文化系统的基本状况,考察其间汩汩流动的灵魂风貌,将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到情的至真、至美之外,还有至善的境界,对人性的提升更有助益。这也是《红楼梦》这部贵族小说的珍贵价值之一。
[1] 孙逊、宋莉华:《“榜”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学术月刊》1999年第11期,页61。
[2] 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7),页238─241。周汝昌:《红楼小讲》,第九讲,页40─42。
[3] 李丰楙:《情与无情:道教出家制与谪凡叙述的情意识——兼论〈红楼梦〉的抒情观》,熊秉真主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私情篇》,页202。
[4] [日]伊藤漱平:《金陵十二钗と‘红楼梦’十二支曲(觉书)》(《金陵十二钗与〈红楼梦〉十二支曲——札记》),《人文研究》第十九卷第十分册(1968年3月),页7─20。
[5] 参[日]合山究著,陈曦钟译:《〈红楼梦〉与花》,《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页119─121;[日]合山究著,萧燕婉译注:《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第三章“花案、花榜考”,页103─136。
[6] (清)花月痴人:《红楼幻梦自序》,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二,页54。
[7] 周汝昌:《红楼小讲》,第九讲,页43。
[8] 第十七回脂砚斋评语,原作“总一园之看”,宋淇认为应是“总一园之首”,乃出于形近误抄;而余英时以为或是“总一园之水”,因草书形近而讹误。见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页325。
[9] (唐)般剌蜜帝:《楞严经》,卷四,赖永海、杨维中注译:《新译楞严经》(台北:三民书局,2008),页167。
[10] 张爱玲:《三详红楼梦》,《红楼梦魇》,页202。此外,朱淡文也认为:“薛宝钗的《情榜》考语也可以基本确定为‘无情’。”朱淡文:《研红小札》第五十条,《红楼梦研究》(台北:贯雅出版社,1991),页187─179。
[11] 冯其庸纂校订定,陈其欣助纂:《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册,页125。
[12] (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三,页69─70。
[13] [美]高彦颐(Dorothy Ko)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14] [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第三章“生命历程”,页135─136;第二章“性别”,页73─74。
[15] 详参欧丽娟:《论〈红楼梦〉中“情理兼备”而“两尽其道”之“痴理”观》,《台大中文学报》第三十五期(2011年12月),页157─204。
[16] [美]M.L.艾德勒(Mortimer L.Adler)著,蔡坤鸿译:《六大观念》,第十九章“随自己快乐而行动的自由”,页152─153。
[17] [美]M.L.艾德勒(Mortimer L.Adler)著,蔡坤鸿译:《六大观念》,第十九章“随自己快乐而行动的自由”,页151─152。
一、“情榜”的规划与人选这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