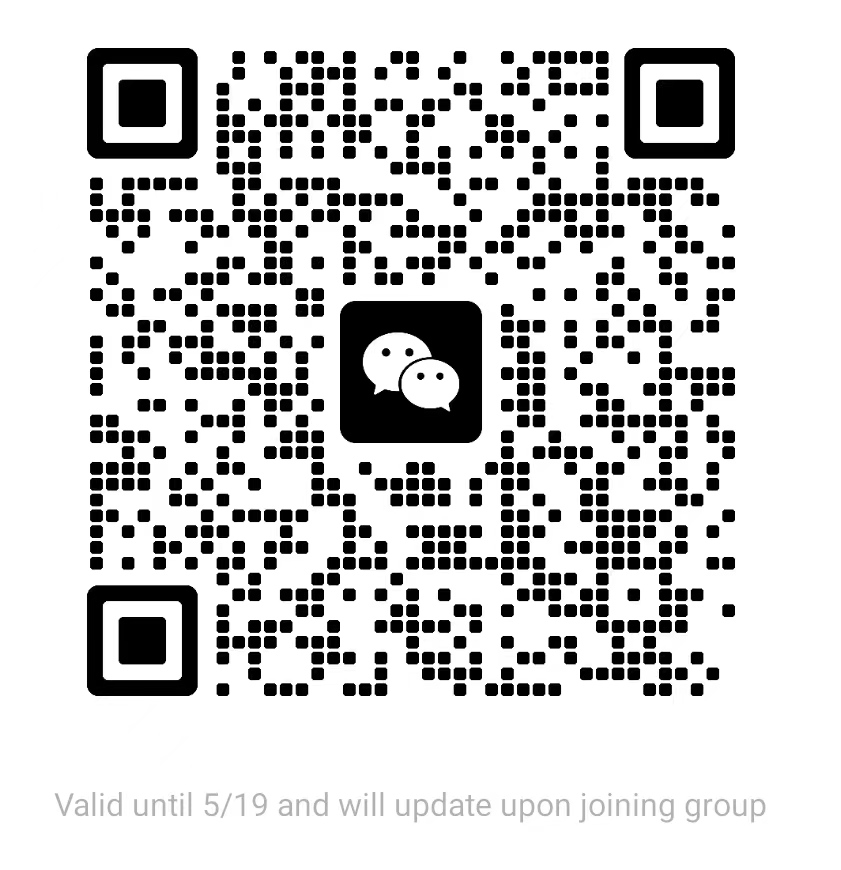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三册 >
- 第八章 贾惜春论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逃避”心理
从《红楼梦》的整体叙事结构而言,迎、惜二春都是到第七十三回、第七十四回始全幅彰示其性格全貌,如果说迎春是“病态的依顺”,因过于随和而藏污纳垢;惜春则是发展出“病态的逃避”,因过于洁癖而冷肃无情,形成背离现实世界的出世心态。
这样一种超离红尘的出世取向,在惜春首度担纲主演的个人秀中一鸣惊人,早早确立了她性格偏执、思想极端的人格特质,由此塑造出她所独具的心智模式。所谓的“心智模式”,是指深植于人们心中,影响一个人对周遭世界的看法,及其所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甚至图像、印象 [7] ,而探本溯源,之所以让年幼的惜春作出如此的憧憬乃至决定,必然有其深刻原因,既是天赋的个性使然,更来自后天的环境影响,亦即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因素。
(一)天赋的廉介孤独僻性
小说家对于惜春的性格特质与心智模式,直到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的相关情节始充分表露。由于那是惜春唯一一次的主场展演,远比和智能儿玩耍一段淋漓尽致,涵藏了其性格特质与心智模式的所有资讯,因此必须仔细检视。当时抄检大队来到藕香榭:
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金银锞子来,约共三四十个,又有一副玉带板子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入画也黄了脸。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了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你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作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好。谁没一个错,只这一次。二次犯下,二罪俱罚。但不知传递是谁。”惜春道:“若说传递,再无别个,必是后门上的张妈。他常肯和这些丫头们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来。
惜春一开始就已经受到抄检阵仗的惊吓,在抖出其丫头入画私自传送收藏物品之际,首先是“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接着则是对这位自小一起长大而情同姊妹的贴身女婢所犯下的情有可原的小小罪过,回应以出奇冷酷的绝情绝义,毫不迟疑地要凤姐“你要打他,好歹带出去打罢,我听不惯”,并严格要求“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次日更坚持将她押解至宁国府,恰巧尤氏来到园中:
忽见惜春遣人来请,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来。惜春便将昨晚之事细细告诉与尤氏,又命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尤氏道:“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竟成了私盐了。”因骂入画“糊涂脂油蒙了心的。”惜春道:“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带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说,又跪下哭求,说:“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儿的情常,好歹生死在一处罢。”尤氏和奶娘等人也都十分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了,下次再不敢的。他从小儿伏侍你一场,到底留着他为是。”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任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
如此不留情面的决绝,表面的理由竟只是因为“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因此面对入画的哭求、众人的说情,惜春完全无动于衷,“任人怎说,他只以为丢了他的体面,咬定牙断乎不肯”。然而,这表面上看似冷血狠毒的铁石心肠,以及爱面子所产生的虚荣心,其实归根究底,都不是造成惜春如此不近情理的真正原因;隐藏在铁石心肠与虚荣心背后的心理根源,乃是一种过于求全责备以致极其严苛的精神洁癖。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过度的洁身自好演化出严苛的道德检验,因此不能容忍无伤大雅的微瑕小错,不接受任何人的人情劝说,不理会犯错者的忏悔求情,不放过共犯结构里的漏网之鱼,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态度下,毫无商量余地地对一切污点进行彻底切割,驱逐悖德的成分。
事实上,由惜春对众人之原宥宽谅入画的决策是“咬定牙断乎不肯”的表现,以及“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的说法,可见惜春并非天生无情冷酷之人,否则何须咬牙以坚定意志,其中自有“舍不得”的动摇。但因一种将其了悟(虽然只是以偏概全的片面了悟)贯彻到底的决心,即使面对“微罪不举”的瑕疵都用道德的显微镜加以扩大,并坚持彻底根绝,以至于旧情虽然温暖可贵,但若夤缘旧情之锁链而来的,是污秽肮脏之世事,那么她也会毫不迟疑地挥刀断绝。对她而言,世界所存在的就是罪恶与污秽,以及罪恶与污秽的可能,因此必须力求斩草除根、除恶务尽,所谓:“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是以惜春不仅在事发当下主动供出相关人犯,更不惜牺牲与入画“从小儿的情常”。
参照第二十二回惜春所作的灯谜诗,以“佛前海灯”为谜底,即大大抒发她对照浊澄源的无上追求:
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身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
贾政看了认为“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净孤独”,因此心内愈思愈闷,竟至难以成寐,而惜春所感受到的“此身沉黑海 ”,不只是比喻整个世界黑暗如海,还回应了佛教的观念。例如王维《过香积寺》所说的“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运用《涅盘经》中的典故:“但我住处有一毒龙,其性暴急,恐相危害。”“毒龙”意指妄心痴念,会干扰甚至破坏内心的平静,而王维将毒龙意象安置在潭水中,惜春则更扩大为“黑海”,可见对惜春而言,整个世界都是黑暗无边的幽暗深渊,各色毒龙处处兴风作浪,吞噬所有的光明。可以说,会如此看待世界的意义,首要的便是那“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也就是与生俱来、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精神洁癖,故探春也说:
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过,我们再傲不过他的。(第七十五回)
“孤介太过”的僻性也就是“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正是惜春思想性格的先天原动力,也是出世选择的基本条件。
王国维曾针对小说中的出家区分为两种意义,认为:
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和平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 [8]
意思是说,惜春的欲求解脱是出于观他人之苦痛,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乃是生活永远必有苦痛,因此断绝其生活之欲,属于宗教的、和平的解脱,是超自然的、非常人的表现;比起宝玉是因为深陷于个人的苦痛,自然想要解脱,而在挣扎的过程中带有悲戚之感,属于人类的自然表现,惜春要来得高明百倍,也困难百倍。
但这种解释适用于宝玉,对惜春而言则并不切合,如此幼小的女孩很难也确实不具备那种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的非常之知力。反倒是王蒙的说法较为接近,他指出:与柳湘莲、芳官以及中外寺院里众多“在失去了红尘的幸福以后看破红尘”者流不同,惜春乃是由于“一种近乎先验的对于红尘的污浊的恐惧 ,一种相当自私的洁身自好(例如,失窃后她并不关心家庭受到的损失而只关心自己的面子)而出家的”。 [9] 其中所谓的“相当自私”“只关心自己的面子”并不切当,请详下文的说明;除此之外,“一种近乎先验的对于红尘的污浊的恐惧”则可说是深深探得其中肯綮,实为对惜春“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的绝佳解释,也正与灯谜诗的“性中自有大光明”相互定义。
(二)奇特的独立宣言
但必须说,天性只是形成性格特质的因素之一,“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只能部分地解释这种以出家为终极追求的独特世界观,若无后天环境的激发与强化,“孤介太过”的僻性未必足以巩固出家之路。
试看惜春为了杜绝任何一丁点的污染,不惜六亲不认,其决绝更从贴身丫头扩大到整个原生家族,由“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的道理,来和宁国府之亲族手足划清界线,以断绝污浊因子入侵的机会与可能性,可见这个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所谓:
更又说的好:“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近日我每每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 。……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 ,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古人说的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 够 了,不管你们 。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尤氏听了,又气又好笑,因向地下众人道:“怪道人人都说这四丫头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方才一篇话,无原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虽然是小孩子的话,却又能寒人的心。”众嬷嬷笑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要吃些亏的。”惜春冷笑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所以都是些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说我年轻糊涂。”尤氏道:“你是状元榜眼探花,古今第一个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尤氏笑道:“你倒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讲起了悟来了。”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惜春道:“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 。’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 !”
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羞恼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上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今见惜春又说这句,因按捺不住,因问惜春道:“怎么就带累了你了?你的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我倒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些话。你是千金万金的小姐,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 。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惜春道:“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清净 。”(第七十四回)
这一番长篇大论有如割裂宁府血脉脐带的独立宣言,正式与宁府以及府中家人断绝往来。
可见惜春这株“尚未识事”的幼苗对世间必然存在的黑暗面避之唯恐不及,为了彻底阻绝可能波及自己的不洁与罪恶,深怕稍一松懈便坏其全璧,导致过分地全力发展她唯一可以依恃的精神武器—亦即自己对“干净”的坚持,在过犹不及的情况下,终于成了一个“只有躲是非”、怕被不堪之事“编派上”“带累坏”,而“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的“自了汉”,那不近人情的“心狠意狠”即是她用以自渡的唯一方法。其所自力建构的思想体系或理论基础如下:
了悟=明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的道德自决→舍得→狠心人→自了汉
与迎春所言的每一个句子都带有一个否定词,以指向意志、能力的自我否定者相反,惜春话语中的否定词虽然也是根源于生存的极限,却都是指向对外在世界的否定,并导致个人存在关联的断裂与抽离,所谓“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以及“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种种说词恰恰正显出惜春的出世思想是自了,而不是渡众;是冷肃无情,而不是宽和慈悲,其人间的生活形态和观照心态带有愤世嫉俗的悲观本质,属于佛教观点中侧重否定工夫,而以消极方法制止妄动、断除迷误的“小乘根器”。
同时从中可知,惜春所发展的乃是一种极为简化的世界观,其中蕴含的人生体验或世界认知是为一种只有“洁净”与“污浊”的极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非干净即肮脏,除此之外容不下其他的价值层次,也因此丧失了回环涵容的弹性空间,与其他人生景观的开拓。其极端简化的二元价值观或世界观可由下表显示之:
洁净、光明↔污浊、黑海
空门↔宁国府、世界
出世↔入世
应该进一步分析的是,这种对红尘俗世的否定态度当然不会凭空产生,而必有其相应对象所促成。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态度”的定义甚多,其中最完备的定义是将态度视为个人对特定对象(人、事或物)所持有的一套有组织的认知、感情及行为倾向; [10] 换言之,态度是个人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一套复杂而稳定的心理反应,所以,态度必有对象。 [11] 然而,一个绣户侯门的千金,几乎没有踏出过家门的女童,何以会对红尘的污浊产生如此深重的恐惧?就此,惜春那“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的养成,其实除了与生俱来的精神洁癖之外,还有赖于后天环境的助长强化,尤其对稚幼无知的孩童而言,家庭即等于全世界,家事即等于天下事,家庭人事的环境影响必然是形塑孩童认知的主要力量。
小说中透过旁人的描述,可知惜春的出身背景是:
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唤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第二回)
四姑娘小,他正经是珍大爷亲妹子,因自幼无母,老太太命太太抱过来养这么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第六十五回)
可见惜春的血脉本源乃是宁国府,与贾珍为一母所生。然而宁国府可以说是贾家的罪恶渊薮所在,是这个百年贵族世家精神堕落的祸首,第五回有关秦可卿的描述就一再指出这一点: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人物判词)
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红楼梦曲·好事终》)
而惜春竟与“造衅开端 ”“家事消亡 ”的宁府血脉相连,尤其“爬灰”的贾珍更是她的亲哥哥,具有完全相同的骨血基因,对于一个天生洁癖的人势必造成无法摆脱的原罪意识;尤其在自幼被抱到荣国府照顾,有贾母、王夫人这样正派温暖的大母神悉心养育,有宝玉、众姊妹如此清新优雅的手足相濡以沫,更对比出宁府的污秽不堪,如柳湘莲跌足所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第六十六回)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小女孩而言,理应带来很大的压力。清代评点家二知道人即认为:
惜春幼而孤僻,年已及笄,倔强犹昔也。宝玉而外,一家之举止为所腹非者久矣,决意出家,是父是子。 [12]
许叶芬更清楚指出:
惜春天性孤僻,其遣入画一事,诚为过当。然观其对尤氏之言曰:“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如何教你们带累坏了。”厥后之出家佞佛,未尝非境遇激之也。柳湘莲诮宁府惟有石狮子干净,呜呼!如四姑娘者,殆可与狮子比洁矣。 [13]
其中都已经注意到环境因素对惜春出家的影响,唯二知道人所谓“宝玉而外,一家之举止为所腹非者久矣 ”,其实是不正确的说法,惜春所“腹非 ”—也就是心中默默批判的对象,以及“境遇激之”的境遇,都是来自宁国府,并非宝玉之外的整个贾家成员。由此可见,惜春的极端性格确实与其原生家庭密不可分。
心理学家霍妮认为,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或适应不良所致的病态人格,乃肇因于基本焦虑,而其潜因于儿童期即已形成;亦即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作为一种以为自己“渺小、无足轻重、无助无依、无能,并生存于一个充满荒谬、下贱、欺骗、嫉妒与暴力的世界”的感觉,乃源于童年时父母未能给予他们真诚的温暖与关怀(往往由于父母本身的病态人格或缺陷),使这些孩子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觉”所引起。而由于无条件的爱是儿童正常发展的最基本动因,因此那些未能得到这种爱心的儿童,即觉得这世界、周围环境皆是可怕、不可靠、无情、不公平的,这种怀疑倾向使他觉得个人被湮灭,自由被剥夺,于是丧失快乐而趋向不安。同时一方面,儿童因为年纪尚轻,虽然对父母的爱心怀疑,但却不敢表露,害怕因此受惩罚与遗弃,这种被压抑的情绪导致更深的焦虑,结果在这种充满基本焦虑的环境中,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自尊自助丧失;儿童为了逃避此种焦虑并保护自我,于是形成病态人格倾向。 [14]
就霍妮所区分的几种病态人格倾向中,惜春发展的则是“病态的逃避”(Neurotic Withdrawal)此一病态人格倾向。其心理状态犹如霍妮所指出,儿童越是与他人隔绝,就越是会将其对自己家庭的敌意投射到外部世界,从而认为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危险和威胁,形成一种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为焦虑的主要根源与直接原因; [15] 此种情绪基于病态的相信:“如果自己能自足,就可以安全 。”因而他寻求情感上独立于他人,逃避他人,不但压抑一切感情的倾向,甚至否认感情的存在,对任何事物均冷漠不关心。他的信条是:“如果我逃避别人,他们就无法伤害我 。”而其与他人的适应关系表现为脱离他人(Away from people),这种人的主要基本焦虑是孤独感,他既不希望依属于任何人,也不反抗,只想远远的躲避他人,“与世无争”。“求生活安全”大约可以概括之。 [16]
从“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第七十四回) ,清楚显示了惜春是胆小易受到惊吓的,她确实一直处在恐惧之中,足以形成基本焦虑;即使幸运地移居荣府,但宁府仍在一墙之隔如影随形,其中的成员尤其是尤氏等女眷更是往来频繁热络,因此那“生存于一个充满荒谬、下贱、欺骗、嫉妒与暴力的世界”的感觉仍然时时被提醒,以至于觉得这世界、周围环境皆是可怕、不可靠、无情、不公平的。为了逃避此种焦虑并保护自我,于是形成了“病态的逃避”的人格倾向,认为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危险和威胁,从而形成一种基本敌意,寻求情感上独立于他人,这些特点都充分表现于惜春一再宣说的:“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上了”“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的”“我只知道保得住我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有事别累我”,以及“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在在印证了潜藏在种种说辞之下的,乃是“如果自己能自足,就可以安全 ”的信念。
而在儒家伦理笼罩整个社会的群体结构里,一个对原生家庭充满敌意的小女孩,为了追求安全所选择的“自足”方式以及脱离他人的极致,则只有出家一途。这便是惜春执意为尼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