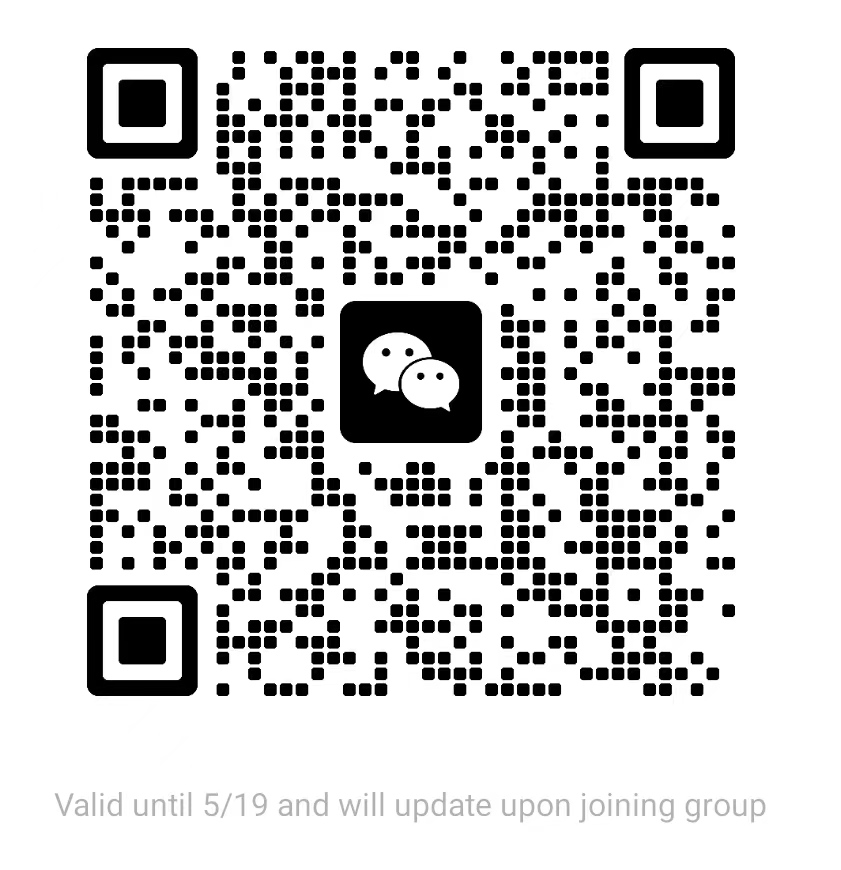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二册 >
- 第六章 贾元春:大观天下的家国母神
一、“枝头第一春”:命名与意义
首先从命名来看,乍看之下难免从俗的“元春”二字,其实大有深意。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段中,冷子兴对贾雨村说明道:
“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这就奇了,……政老爹的长女,名元春,现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贾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上一辈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
可见这乍看之下未免流于俗艳的从春之名,其实意义深长,来自罕见而特殊的生日。“生日”对一个人来说实为重要,不但是自己在世界上赖以定位的一个基本座标,其中还隐含了许多关于人生的讯息密码,因此忘记生日或没有生日的人通常是不幸的、漂泊无依的,香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反地,特殊的生日往往联系到特殊的人,元春就是这一类的典型。
首先,从为人之始以观之,元春之出生即带有浓厚的圣诞意味,故由此“名元春”。这种带有特殊意义的生日,被小说家用来寄托极为重要的象征,尤其是就一个女孩子而言,婚姻可以说是终身幸福所系的人生大事,而婚姻的缔结又与生日有关,如第五十回贾母有意求亲于宝琴,做法就是向薛姨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又第五十七回宝钗提到哥哥薛蟠还没有定亲,黛玉揣测的原因便包括“或是属相生日不对”;而第七十二回贾琏也提到“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这是因为两家议婚的时候需要拿庚帖合配男女双方的八字,那代表着上天的超越性的指令,因此也带着预兆的作用。学者就指出:“在清朝的上流社会,几乎所有的年轻女子预期自己将成为别人的妻子。打从女儿出生开始,父母便进入了一个高度紧张的过程,不仅必须调教女儿、使她为婚姻做好准备,还得准备嫁妆。就连她的生日也具有预兆的性质,因为在挑选未来夫婿的时候,必须将两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拿来比对。”[1]于是,小说家就利用元旦这个特殊生日来寄托至关紧要的象征,从婚配的角度来说,便暗示了元春的夫婿会是极尊贵的人,而后来证明了这个极尊贵的人正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第十六回传来入宫为女史的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从此就由元春变成了元妃。以世俗价值观而言,晋封贵妃之荣幸当然是福大之至的盛事,因此探春在谈到家人的生日时,也说道:
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也有三个一日,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日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第六十二回)
这即是第五回判词中所说“三春争及初春景”之意,“争及”是“怎及”“岂及”“哪里比得上”的疑问否定词,整句诗意指迎春、探春、惜春(也代表了其他的所有金钗)都比不上元春的繁花盛景。而元春领先群伦之地位就隐含在诞生于大年初一的时序中,由于大年初一是宇宙循环的开端,大地更新、万物死而复生,普天同庆,春回人间,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中,一年一度的新年仪式便是对创世神话的象征性重演,因此生日在这一天的人便属于“神圣诞生”的特殊人物。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她同一天生日的还有“太祖太爷”,亦即为贾府创建百年富贵基业的荣国公贾源(见第三回,第五十三回则作贾法)。所以可以说,大年初一不但是全国性最重要的节日,还更是贾府自家所专属的圣诞节,贾源作为擘创家族富贵基业的伟大祖先,他的生日就等于是所有族人的共同生日,因此是举家同庆,元春恰恰出生在这一天,既是巧合,更是命中注定。因为出生在同一天的人似乎有某一种特殊的联系,姑且不谈命理学、占星术的神秘说法,单单以文学的象征手法而言,小说家就充分利用了这种关联性,为他笔下的人物之间建立某种呼应关系。例如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在抄检大观园之后,又特来亲自阅人,从袭人起以至于极小作粗活的小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应,老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作四儿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固然这是主仆之间私下毫无避忌的玩笑话,却的确反映出同一天生日的特殊联想。而事实上,与宝玉同一天生日的薛宝琴,正是贾母唯一开口为宝玉提出婚配的人选,虽然因为宝琴已经订婚而作罢,若从象征意义来说,二宝仍算是“潜在的夫妻”。
当然,元春和创业祖先同一天生日有其他意义,是建构在百年家族命运薪火相传上,为家族建功立业的继承关系。荣国公贾源加官晋爵创造了贵族世家,元春则是入宫封妃,由贵族进一步提升为皇亲国戚,更是光耀门楣,把宁、荣国公一手打造的贾家带到登峰造极,所以有资格和祖先共享同一天生日。如此一来,元春也就等同于晋身为家族的母神了。这是元春身为母神的第一个象征。
在封妃之前,元春首先是“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去了”,这是入宫的第一步,正是当代旗人社会中“选秀女制度”的反映。
“选秀女”是一种为皇室后宫提供年轻女性,作为指婚对象(妃嫔)和服务人员(宫女)的选拔制度。清代所选的秀女都是来自旗人,而随着外八旗与内三旗的两个不同系统,清代的选秀女制度也分成两种管道,按《国朝宫史》所言:
凡三年一次引选八旗秀女,由户部奏请日期。届日,于神武门外豫备,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关防,以次引看毕,引出。……凡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届期,由总管内务府奏请日期,奉旨后,知会宫殿监。宫殿监奏请引看之例同。[2]
明确可见两者分属不同的系统,彼此互不相干。然而,除阅选的频率不同外,两个管道所选出的秀女也有不同的用途,这才是最大的差别,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其一,八旗满、蒙、汉军正身女子,年满十三岁至十七岁者,每三年一次参见验选,选中者,入宫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验选前,不准私相聘嫁。其二,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亦选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可见,同样是选‘秀女’,八旗女子和内务府女子中选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内务府女子被选入宫,多充当杂役,满二十五岁才能遣派出宫。[3]为皇室无偿服役十余年,按当时标准,出宫时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谈何容易?内务府女子不乐入选,乃人之常情。”[4]
从这两种差别来说,元春的“选入宫作女史”,似乎并不是八旗系统的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再参照宝钗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第四回写到宝钗之所以来到贾府,便是因为:
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这段话可以说是元春入宫的进一步补充。而同样地,宝钗的“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是在“聘选妃嫔外”的另一个不同的管道与功能,并不是作为皇子王公的指婚,这说明元春与宝钗的入宫是属于内务府包衣三旗的选秀女系统,较偏向宫女性质。再者,以元春的入选条件是“贤孝才德”,宝钗所应选的是“公主郡主入学陪侍的才人赞善之职”,都属于以才学和贤德为重的高等女官,所以元春刚入宫时的职任就雅称为“女史”,绝不是捧茶递水之类的女仆。如此一来,元春封妃的际遇可能是历史记录中,由内务府三旗所选出的秀女晋升为妃嫔的少数例子,如学者所指出:“有清一代,内务府三旗女子通过选‘秀女’晋身嫔妃者代不乏人,其母家一跃而为皇室戚畹,父兄子弟多跻身枢要。”[5]但也可能是融合了外八旗与内三旗这两种管道的虚构,无论何者,以元春封妃强化贾府的荣盛等级,这是小说文类的虚构本质所允许的,而“十三岁”应该就是元春入宫时的年纪。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所谓的“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凡”与“皆”这两个用字,清楚指出“选秀女”是所有相关家庭都必须遵守的义务,不是个人意志所能选择决定,违逆不得,也谈不上争取;而贾、薛两家的闺女都属于内务府包衣三旗的选秀女系统,较偏向宫女性质,入宫的目的并不是指婚为嫔妃,已见上述。从这两点来看,元春的封妃属于非比寻常的机遇,是意料之外的荣宠,所以脂砚斋说这是“泼天喜事”(第十六回眉批);而宝钗的入京待选也完全谈不上存有追求飞黄腾达的野心,只不过是遵行朝廷规定的义务而已。这是我们应该先了解的基本历史知识,对于正确理解人物的性格至关重要。
被明熹宗选定为皇后的张嫣,其容态是:“厥体颀秀而丰整,面如观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鬓如春云,眼如秋波,口如朱樱,鼻如悬胆,皓齿细洁,上下三十有八。丰颐广颡,倩辅宜人;领白而长,肩圆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轻云之出远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诸病。”[6]清代遴选后妃的标准虽不中亦不远矣,元春既得以封妃,诸如此类的美貌自不待言。而除容貌外观之外,选秀女的主要标准更是才德与门第,元春本身必然都具备这些入宫封妃的重要条件。其中,国公世袭家族已经先天地满足了门第的要求,另外,才德的条件当然也不可或缺,所以才会先是担任女史,再后又封为贤德妃,而“才德”也确确实实是元春之所以能成为贾府第三代母神的最伟大之处。
因此,判词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不只是从世俗的身份权位而言,也意味着元春的品格才德超过了三春,甚至可以说,通过了皇宫的严苛考验,她的完美性格较诸宝钗更胜一筹。
宫廷采选秀女之严格制度,使得妃嫔们都是经过无情淘汰之后的精华上乘,无论在身心各方面都是合乎最高标准的一时之选。至于选秀女的标准,我们可以从客观的历史实况来把握,清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便描述其规模道:从最初之五千人历经数道程序,以至范围缩小到“入选者仅三百人,皆得为宫人之长矣。在宫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论,而汇评其人之刚柔、愚智、贤否,于是入选者仅五十人,皆得为妃嫔矣”[7]。这里所说的虽然是明朝的选妃状况,但由于明清两代都有采选秀女的制度,多少有近似性,若以此一准则衡量《红楼梦》所根植的社会环境状况,应可提供一个合理的参照系。则元春既然是“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随后又进一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所有的遴选条件都聚焦在“贤孝才德”上,浓缩简称的“贤德”甚至是她的正式封号,可见其封妃的主要条件就是“贤德”。
然而,“贤德”又是什么?从字面来看,就是沉静贤良之妇德,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雍容华贵之气度。但言及贤良的妇德,现代读者很可能又从抽象的成见联想到迂腐、死板、僵化、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标签,其实却全非如此,元妃的贤德来自于崇高的人格与智慧的体现,是融合了先天资质与后天修为所形成的一种内在涵养。其贤德的表现之一,就是“富贵不能淫”的人格厚度。
“元春”,《程甲本红楼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品。
(一)富贵不能淫
《孟子·滕文公下》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如果不拘泥于性别,而单就人格判准来看孟子对“大丈夫”的定义,这三种境界都能产生难能可贵的伟大人格,一般人也都不容易达到。但若一定要强分出难易程度,或许“富贵不能淫”才是最大的挑战,原因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两项都有特定的对象,最关键的是其性质也都属于外来的压力,在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既容易察觉,也比较容易集中心力进行对抗,只要咬紧牙根、立定脚跟“不移”“不屈”,就可以守住人格阵线。
但“富贵”的性质却和“贫贱”与“威武”截然不同。如果说“贫贱”与“威武”对人所造成的是高度的紧张压迫感,那么“富贵”所带来的却是极度的愉悦舒适感,它并不是外来的压力,也没有集中在特定范围,而是一种顺着人性让人通身遍体都极其舒畅的感受,只要放松就可以享受各种权力快感与物质满足。然而,一个人要如何对抗时时遍布于千万毛细孔中的熏风暖意?要如何处处防范围绕于身边所有人事物的友善笑容,以及鼻之所嗅的芬芳气息、耳之所闻的动听声语、口之所尝的膏腴滋味与眼之所见的华丽光芒?而“淫”字所意指的“过度”,其界线又该如何划分?既然不知不觉中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乃人之常情,以致产生19世纪英国史学家兼政治家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于《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所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的现象,“富贵”对人性的影响亦然,因此才会有“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深切观察。则若要守住恰如其分的界线,就必须“时时、处处”省思觉知,以免稍有松懈不察便有所逾越堕失,因此道德自觉与自我克制在时间上更持续、在深度上更沉厚、在幅度上更广延,等于是随时随地的精神修炼。就此而言,所动员到的心理能量和道德力量便相对大增,通过考验的难度也随之相对提高。这就是“富贵不能淫”才是最大挑战的原因。
衡诸元春的人格表现,正堪称是“富贵不能淫”的女中大丈夫。试观她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第四回)的贾家中诞生成长,并没有落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而眼高于顶、骄奢任性,如《颜氏家训》所说:“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8]反而谦逊温厚又朴实真诚,可见成熟大度、稳重和平早已是她内蕴之品格。再看她飞入帝王家,荣获帝王宠幸,晋升为皇妃而恩遇正隆之际,也并未得意忘形地不可一世,利用权势恣意纵情于挥霍享乐之中,反而依然以人伦亲情为贵,以朴实俭约为重。由她含泪对父亲贾政所说的:
田舍之家,虽虀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第十八回)
可知在元春人生价值的天秤上,富贵荣华乃是轻如鸿毛,骨肉亲情则是重于泰山,所看重的正是人生中最本质性的价值。也因此,她在回府省亲时,“看此园内外如此豪华,因默默叹息奢华过费”,并一再劝请“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恰如在游园题撰中,众清客都说的“贵妃崇节尚俭,天性恶繁悦朴”,全然没有一般骄奢之辈的作威作福。单单一门一户的理家权力,就足以使“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第六十二回黛玉语),元春身为天下第一人身边的宠妃,却完全没有被权力腐化,身在绝顶富贵荣华之中更能长葆心灵的朴实无华,真正展现出“富贵不能淫”的淳厚人格,可以说已经达到崇高的君子品性。
除此之外,宫廷位于皇城的森严禁地中,与世隔绝,乃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因此入宫为妃的元春除了返家省亲之外,与贾府的联系只能等待少数宫中会面的机会,如《国朝宫史·宫规》所记载:“内庭等位父母年老,奉特旨许入宫会亲者,或一年,或数月,许本生父母入宫,家下妇女不许随入。其余外戚一概不许入宫。”[9]反映在小说里,则是借由皇帝推己及人的悲悯,“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可见这些可以直接见面的情况是少之又少,且入宫时现场禁锢重重,势必无法随兴尽情;即使蒙恩获准回府省亲,也是偶一为之的蜻蜓点水。整体而言,无论相会之地在于何处,都难以在父母手足的天伦中获得家庭的温暖,以致元春才会伤心悲叹“骨肉各方,终无意趣”(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清光绪己丑年[1889]沪上石印本),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元春大约于十三岁时入宫,她就这样一个人在后宫孤独地度过二十年,从少女到中年,在没有亲人的支援系统之下长期独自面对复杂的生活,若无坚忍不拔的韧性,如何能够承担?身在绝顶富贵荣华之中,而长葆心灵的朴实无华,始终固守着生命中最珍贵的初衷,不离不弃,这是贤德的另一个深厚内涵。
(二)二十年来辨是非
元妃虽然是高贵的君子,却不是迂腐乡愿、可以欺之以方的呆板君子。从她长期生活在宫中“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犹能夷然自处,更必然内蕴一种圆融通透的智慧。
从情理上来看,一个在后宫如此竞争激烈的复杂环境中生活的人,怎么可能是天真无邪的?宫中的真实生活并不是缤纷花园的甜美牧歌,即使是贾府这样的一般贵宦之家,其间利害得失之尖锐险恶,都已经如探春所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而元春居处在后宫中,政治环境的恶劣情况更有过之,正如王维所描述的“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按剑”(《酌酒与裴迪》),连相知到老的朋友都不能信任,何况其他!利之所在,必然驱使各方人马合纵连横,人际关系暗潮汹涌,而且不需要什么恩怨是非、深仇大恨,只要是别人往上爬的绊脚石,就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而欲除之为快,各种陷阱地雷遍布周遭,只等着趁隙而入以便取而代之。即使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我虽无伤人之意,却必须提防人要伤我,这是一个尔虞我诈的人性杀戮战场,因此单单是为了自保,这种防不胜防的情况就同样少不了眼观四面、辨是察非,时时刻刻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判词中所说的“二十年来辨是非”,就暗示了元春自入宫以后的二十年间都处在“辨是非”的步步为营中。在波诡云谲、机关算尽的皇宫生涯里,终日面对的皆是恩怨纠缠、敌友难分而是非混淆的复杂关系,既有朝不保夕的兢兢业业,亦复有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小心翼翼,自不免日日勾心斗角,“辨是非”乃成为在宫廷中立足时不可或缺的基本求生能力。
所以,元春在这二十年中,要辨认敌友,要回避陷阱,要化解暗箭,更要防患未然,正如庄子所说的:“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10]真的是辛苦万分!但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这样的环境中并没有同流合污,养成杀伐奋进、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尖锐性格,更没有把娘家贾府也整合成图谋权势利益的外戚集团,反而把“辨是非”的现实需要与心智锻炼加以转化,升华为圆融的智慧,聪慧而不机诈,智谋而不阴谋,而得以在孤独却复杂的环境中安顿自己,并进而安顿其他的少女。这真是一个聪明睿智又坚忍不拔的贤德君子。
(三)高度判断力
这样的杰出人物,在皇宫如此特殊的环境要求下,自然不会有她的母亲王夫人“健忘”的缺点,但这对母女确实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欠缺高度的文艺才华,王夫人唯一的一次表现,连差强人意都谈不上,比起刘姥姥都还不如。第四十回写贾母领着众人在大观园中游乐,筵席上行酒令的时候,鸳鸯说明行令的方式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错了的罚一杯。”整个过程中,参与者都一一行令,连刘姥姥都即席运用乡野知识依样画葫芦,虽然本色却也合令,只有“至王夫人,鸳鸯代说了个”,可见是和诗词风雅完全绝缘。
元春的情况虽不至于此,但文艺才华也确实不高,从一般的标准来看,元春并不具备黛玉之辈在创作上的“诗才”。
第十八回中,元春于回府省亲时曾向诸姊妹坦承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善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因而自谦仅有“微才”。而的确,于第二十二回中,元妃制作了一个灯谜差人送出宫外,令贾府内大家都猜,“宝钗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而反过来,元春对姊妹们所作的灯谜,则是“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由此种种端倪,可见元春的确不擅于诗词创作,故脂砚斋评论其大观园诗就说:
诗却平平。盖彼不长于此也,故只如此。(第十八回批语)
但是,元春所不擅长的只是诗词创作而已,若就此遽以论断元春资质平庸、乏善可陈,便恐怕不甚得当。如清人涂瀛就批评元春是平凡的庸才,认为: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间,宜其多厚福也,然犹不永所寿,似庸才亦遭折者。说者谓其歉于寿,全于福矣,使天假之年,历见母家不祥之事,伤心孰甚焉!天不欲伤其心,庸之也。越于史氏多矣。[11]
但这段话大有问题,实际上,元春的品貌必然是出类拔萃的,否则达不到入宫的基本条件,前面已经有所说明;而就才情来说,元春所具备的乃是创作之外的另一种“别才”,诚有其洞明开通之处,远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望其项背。
首先,即使仅就诗歌创作的范畴而言,于传统诗论中,也曾区分出“创作”与“批评”的不同层次,而提出一种“吟咏创作”与“鉴赏分析”彼此有别乃至于彼此互斥不得兼备的观点。如南朝刘勰、钟嵘这两位分别以《文心雕龙》《诗品》辉耀千古的诗评家,却都缺乏一诗传世的偏颇现象,正是此中之典型代表;而李白、杜甫这两位旷古大诗人都缺乏严谨的诗论体系,也是出于同一道理。
这是因为创造的范畴,需要的是灵动敏锐的感发品悟与巧妙脱俗的语言表达,属于个人才性的部分,其中天赋的禀性气质占绝对的优势,所以贾政才会说“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第十七回);而“鉴析”却属于评论的范畴,需要的是客观分析的理性能力和综合比较的宽广眼光,有赖后天兼涉博览的学养与宏阔包容的胸襟始能造就。二者彼此不但未必相容,反而还常常具有排他性而发生互斥的现象,使人往往不能一身兼具“善作”与“善评”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能力。如清代诗论家吴乔便提出类似的看法:
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12]
此外,清人陈仅更进一步透过历史经验,归纳出“鉴析”与“创作”这两种能力非但彼此性质不同,尚且具有排挤互斥的关系,认为一人往往不能兼容善作与善评的才性:
问:“钟嵘《诗品》为千古评诗之祖,而记室之诗不传,岂善评诗者反不能诗乎?”“非特善评者不能诗,即善吟诗者多不能评诗。……因知人各有能不能也。”[13]
由此可见,元妃这种“不善作却善评”的情形完全没有矛盾,传统诗论家不但加以认同,还提出理论性的解释,更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现象。
《红楼梦》中,除元春之外,还有李纨是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曹雪芹所塑造的李纨是有德无才的,她在“女子无才便有德”“只以纺绩井臼为要”(第四回)的价值观之下成长,本身也确实是如她所自谦的“不会作诗”“不能作诗”,先前在元妃省亲时众人赋诗志庆的场合中,也仅仅只能“勉强凑成一律”而已(第十八回)。但另一方面,她在诗艺上却并非一无是处,虽然素乏创作上的诗才,却无碍于诗社盟主的担当,而且最具有掌坛的资格,根本的原因乃是宝玉所指出的:
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第三十七回)
由随后众人对此话的应和,所谓众人都道“自然”可知,李纨品第评阅的眼光与客观公正的态度早已受到众人一致的认可,因此众望所归,成为海棠诗社的掌坛盟主,具有威服众人、一言九鼎的权威。
同样地,元春显然与李纨一样,都属于“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的文学批评家,虽无创作的才华,却无碍于品评鉴析的高度眼识。她的评鉴能力,使她在省亲时,对众人所作的诗一眼就看出其中的才华,先是赞美“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继而又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诸诗中慧眼拔擢林黛玉之作品,指出黛玉作枪手替宝玉代笔的《杏帘在望》一诗“为前三首之冠”,完全合乎宝玉所认为的“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过十倍”的评价,以至元妃甚至不惜出尔反尔,特别因为黛玉的这首诗而将御制的“浣葛山庄”改名为“稻香村”(第十八回),可见她对黛玉诗才的把握乃是同样精准,展现出合乎情实的真知灼见。据此,清人青山山农的一段话十分值得注意,他指出:
元春才德兼备,足为仕女班头,惟是仙源之诗,知赏黛玉;香麝之串,独贻宝钗。后此之以薛易林,皆元春先启其端也。世无宝玉,其谁为颦儿真知己哉?[14]
很显然,青山山农虽然还是不免囿于右黛左钗的传统成见,而认为元春是“以薛易林”的始作俑者,并判断元春并非黛玉之知己,但已难能可贵地注意到元春“仙源之诗,知赏黛玉”的一面,准确把握到元春“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的鉴赏才能。
何况进一步来说,“诗才”并不只是创作上的才能,还包括鉴赏评论的眼光;更必须说,诗才也不过是人类各种才性能力中的一种而已,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本就不必限定在文艺表现上。从这个角度而言,元春的“才”就和王夫人的“将将之才”一样,都不是一般意义下如王熙凤的干才或林黛玉的诗才,容易引人注目,而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与穿透复杂的洞察力,并且和贾母、王夫人一样,拥有高度的识人之明。
以“鉴赏评论的眼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而言,小说中一再写到:“贾妃见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贾妃看毕,称赏一番,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对于宝钗的容貌丰美、鲜艳妩媚以及诗风的雍容典雅,和黛玉的纤细飘逸、风流袅娜以及诗风的清新脱俗,都给予毫不保留的赞美,既不偏好宝钗,也没有独重黛玉,这已经显露出一种兼美并善的宽广视野,由此对于为两人量身订做的潇湘馆、蘅芜苑二处,元妃也同样表示最大的喜爱,其中自有一贯的道理。然而其胸襟并不仅仅如此,试看她对大观园的各个重要景点所作的表示:
此中“潇湘馆”“蘅芜苑”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
这段话所隐含的重要意义,在于元妃的审美光谱无比宽广,她的心灵所能够回应的频率或弹奏的音域是没有局限的,因此对风格截然不同的四处场所兼容并蓄;相较起来,其他的人物则各有所偏,因此也都难以处处见美。例如性情最为偏至的林黛玉仅独沽一味,当入迁大观园时即表示潇湘馆是她的唯一选择,笑道:
“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和我的主意一样,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第二十三回)
而宝玉显然是除怡红院之外,也只喜欢潇湘馆,尤其对稻香村最是敬谢不敏,还一反平素畏父如畏虎的怯懦,在贾政面前高谈阔论,以潇湘馆为典范,发挥了一大段对稻香村的批评: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第十七回)
此中显示出宝玉对于真正的、全面的“大观精神”认知不足,所以才以他个人的偏狭理解对稻香村的设置有所非议,这一点请参本章第四节“大观园的擘建与意义”的相关分析。至于蘅芜苑,连贾政的评论都是:“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第十七回)而贾母也期期以“雪洞”般的布置风格为不可(第四十回),应该是更不得二玉的欢心。可见每一个人都处在某一种或某一些特定的框限里,各有所见,也各有所限。然而,元妃却是远远超越了众人的好恶取舍,对潇湘馆、蘅芜苑、怡红院、稻香村这四处一体赏爱,虽不免稍有甲乙之别,却都在“所爱”的范围内而名列前茅,如此一来,岂非正证明了元妃的审美光谱和心灵音域最是兼赅全备,能够与世间的各种美、各种价值相共鸣、相应和?
因此,第十八回当元妃看毕众钗的应制之作后,除评比高下之外,“又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出令太监传与外厢。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不仅如此,接着于第二十三回“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叙其优劣”,并进一步“又命在大观园勒石,为千古风流雅事”,将这些诗作刻在石碑上,永远留存于大观园中辉映增光。可见元妃对省亲时姊妹们所作的大观园题咏极其珍爱,视之为“风流雅事”且足以与金石同其不朽,对这些诗篇只有纯粹的欣赏、无私的赞美,则其心怀中的一段性灵不也是盈溢焕发?她虽不是一流的杰出诗人,却是诗人们最大的知己与保护者。
事实上,元春“善看又最公道”的能力于识人之明上更显突出,“善看”的眼力、洞察力,让她一则是欣赏优秀的女性,如宝钗、黛玉、龄官等;二则是知人善任,在宝二奶奶的人选上由宝钗雀屏中选。
首先,对于宝钗、黛玉、龄官之类优秀女性的欣赏,主要是表现在省亲之时。她特别称赞说“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对于龄官,则更是谕令说“龄官极好”,并给予额外恩赏,这和宝玉“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第三十六回)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元妃在省亲现场与回宫后的两次处理大观园题咏,一次是现场“命探春另以彩笺誊录出方才一共十数首诗”,一次是回宫后“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都是将她珍爱至极的诗篇交给探春抄写誊录,可见对探春的信赖倚重,并且符合探春房中“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第四十回)的习性与专长。而元春既无暇一一叙旧,此际也还是探春韬光养晦的沉潜时期,未及绽放理家时的光芒万丈,却能够知人善任、量能尽才,必然也是看到探春“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第三回)的不凡内蕴,诚亦属识人之明的高度展现。
至于在宝二奶奶的人选上,更是关系重大、牵涉甚广,比起文艺才华的高下还要复杂得多。钗、黛取舍的结果,必然涉及元春之价值观与鉴识力等问题,而价值观与鉴识力都出于个人之才性气质,彼此又往往具有连带关系,价值观之偏向、鉴识力之高低、才性气质之清浊,都会直接影响其判断与决策的结果,必须进一步深入说明。
(四)“舍黛取钗”的原因
就宝二奶奶人选上钗、黛取舍的课题,“以薛易林”确实是明显存在的事实。整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可以寻绎出元春对钗、黛取舍之倾向者,约有隐显不等的三处情节。
依序来说,第一次、也是最奥妙的一次,却又一般较不受注意的安排,乃是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将宝玉所偏爱的“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又删除“绿玉”并偏取“怡红”一词,即名曰“怡红院”这一项施为。要了解其中的奥妙,必须溯及宝玉为怡红院命名的过程,当时大观园刚落成,贾政带领众人游园题撰,原本宝玉题曰“红香绿玉”,乃是着意于院中同时植有海棠、芭蕉,认为必得如此命名“方两全其妙”(第十七回)。也因此,在元春省亲之际,宝玉应皇妃之命赋诗志庆时,于《怡红快绿》这首诗中就一再反覆加以强调,说道: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青烟。
在此四句之下,脂砚斋各自批以“是蕉”“是海棠”“是海棠之情”“是芭蕉之神”之评语,可见其双全兼备的苦心;并且诗句中分别穿插绿、红、绛、青的色泽,在在可见得力于律诗之对仗法则,宝玉不畏冗赘地一再强调红绿相间、蕉棠两植的二元衬补思维。而此中隐含的价值观,又直接呼应第五回神游太虚幻境时所遇到的一位“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的女子,其“兼美”之名恰恰与此处“两全其妙”之说相对应。这都意味着宝钗、黛玉这两种不同人格特质的兼备两全,才是最均衡完美的生命境界,也才是宝玉所追求的理想形态。
然而,这样两全其妙的兼美理想却遭到了片面的否定。元春将“红香绿玉”改名为“怡红快绿”,使得代表宝、黛共有的“玉”字初步遭到删除;接着又进一步化约简称为怡红院,则连用以展现芭蕉痕迹的“绿”字都渺不可寻,导致海棠红香一枝独大的局面。后来宝玉受命应景作诗时,于有关怡红院的草稿中再度使用“绿玉”一词,恰巧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他道:
他(案:指元妃)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罢。……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第十八回)
从字句之间,我们已可以觉察到,宝玉之所以二度使用“绿玉”一词,并非偶然糊涂所重蹈的覆辙,而似乎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表露出来的情感取向,因为所谓的“绿玉”者,实即“黛玉”也。“黛”本是一种深绿色的染料,其色近黑,妇女可以之代为画眉之用,第三回宝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中亦有“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之语,则“绿玉”与“黛玉”便具有颜色相近与成分相通的性质,而指向于“玉石”所禀赋的神性层次。如此一来,宝玉在有关怡红院的命名和题咏上一再偏好于“绿玉”一词的现象,就似乎隐喻着对“黛玉”的执着偏爱。[15]
当然,宝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贵妃姐姐有所不满,因此这段巧妙的情节毋宁是曹雪芹在幕后的刻意安排,用来展现出元春与宝玉的品位差异,以及两人不同的性格取向及其所必然产生的不同选择。
第二次的“舍黛取钗”,是第二十三回元妃决定将大观园开放予众女儿迁入时,所下的谕令乃是以“宝钗”为总提,所谓“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隐隐然可以见出宝钗代表众钗、领袖群伦的优势地位。
至于第三次,也是最明显、最重要的一次,则是表现在赐礼的落差上。先前在第十八回元春初次省亲时,所赏赐的赠礼中尚且将宝钗、黛玉、宝玉与诸姊妹列为同等,给予完全相同的品项;但到了第二十八回的端午节赐礼时,独独只有宝钗的节礼项目与宝玉一样,而黛玉所得的品项则降了一等,仅仅与诸姊妹同级,使宝玉不免疑惑道:“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第二十八回)至此,“金玉良姻”的现实基础已经明显浮现,其取舍的旨意已是十分明确。
这一“以薛易林”的明确表示,让许多读者自然地认定元妃对黛玉孤高不驯的性格感到不悦甚至厌弃,以致在遴选宝二奶奶的取舍中将黛玉淘汰出局。不过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固然以元妃犀利精准的识人之明,于当场察言观色的过程中,应该会对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的高傲心态,与“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的敷衍态度,以及“未得展其抱负,自是不快”的愤懑情貌都看在眼里,黛玉之争强好胜与任性骄妒都堪称历历在目。既然对于黛玉素来“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第五回)、“本性懒与人共”(第二十二回)的性格,连脂砚斋都毫不讳言“此是黛玉缺处”(第五回夹批),元春自当心知肚明,但是,要判断她是否因此而产生成见或反感,则必须参照书中其他的相关情节才能获得更坚实的论断基础。就此而言,龄官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参考座标,足以进行同质性的比较,而提供有力的解答。
客观地说,龄官的种种人格特质,包括容貌、才情、性格、痴情、孤弱、多病等方面,都与林黛玉差相仿佛,从“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态”的形貌身姿,“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的住熬煎”(第三十回)的柔弱禀性,以及多心歪派、折磨贾蔷的苦恋形态(第三十六回),在在都呈现出与林黛玉高度叠合的现象,因此在小说中被设定为黛玉的重像之一。清人涂瀛就说:
龄官忧思焦劳,抑郁愤懑,直于林黛玉脱其影形,所少者眼泪一副耳。[16]
而这两人也都毫不掩饰地直接表露自我,旁人要掌握她们的性格实为轻而易举,对元妃而言更是一目了然,当下立判。然则,龄官这位骄傲的女伶以她的精湛演出与高傲性格,却深获元妃额外的欣赏甚至鼓励,而不是嫌厌不喜,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是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在伶人搬演诸戏之后的一段情节,作者描述道:
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谁是龄官?”贾蔷便知是赐龄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龄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作《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扭他不过,只得依他作了。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缎、两个荷包并金银锞子、食物之类。
由这段描述可知,元春具有对艺术品鉴的非凡眼光与对秀异人才的高度洞视力,在短暂有限的演出时间与为数众多的十二个女戏子中,辨识出龄官超凡绝伦的优异才华,因此特别加以赏赐,赋予她一种几近于御笔钦点般的无上荣耀。其次,元春不但以“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之御旨,赋予龄官自由发挥的宽阔空间,甚至当龄官随后应命演出,却坚持己见,对于贾蔷以主管的权威所指派的《游园》《惊梦》这两出,因非本角之戏而执意不作,定要执着己长,演出《相约》《相骂》,贾蔷扭他不过,只得依他作了。从作者紧接着就写“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可以推知元春对于这段曲折显然完全知悉,且对如此叛逆抗命的表现非但不以为忤,相反地,她所产生的竟是“甚喜”的反应,因此特别谕令不可为难了她,同时更加以额外的赏赐。
且此事并非孤立发生,随后在元春回宫之后又重演了一次。根据第三十六回的记载,龄官对央求她唱戏的宝玉正色拒绝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将这两件事加以并观,可见龄官当着权贵之面勇于抗旨违命,不迎合也不谄媚之性格十分一致,足为其人格构成的一个主要表征。但是,这固然显出龄官率真任情、不同流俗的一面,却也同时表现出矫奇傲岸、唯我独尊的骄纵习性,如脂砚斋即批云:
按近之俗语云:“能(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优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不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子弟广矣,各各皆然。……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姣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第十八回批语)
而元春既然对龄官的高傲倔强都能够加以欣赏,并且护惜有加,使之不受压抑束缚地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那么同理可推,对素来“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本性懒与人共”的林黛玉,也该当如此。
如此一来,其实并不能推衍出元春敌视或贬抑黛玉的论点,从元春对黛玉之重像龄官多方欣赏、包容、鼓励的现象,甚至应该得到相反的论证。那么,对元妃最后作出了舍黛取钗的选择,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在于:元春所具备的乃是一种情理兼备而公私分明的性格,在无关大局的情况下,她可以顺任主观的情之所钟,由衷对鲜明寡合之个性倍加欣赏爱护,因为深知这种人格情态在现实世界中的稀有与特殊;但一旦涉及公众群体之利害关系时,便会发挥自我节制的理性力量,抽离个人的主观偏好而选择客观所需,从整体性的长远持久与平衡稳定着眼。这两种态度并不矛盾,也毫不冲突,理由就在于,她的欣赏包容是出于“自然的理想主义”的角度,对受之于天的禀性气质加以了解与认同,属于个人之主观范畴;而她的淘汰舍弃则是出于“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角度,寻求社会运作机制的维持与促进,属于群体之客观层次。两者并不相混。因此比较其前后两次的赐礼所呈现出来的落差,可见发生变化的关键并非元春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在个人主观好恶之外攸关大局的客观考量。
至于所谓“客观考量”,无非就是以家族利益、团体和谐、人际调节、族群延续等群体需要的角度所作的判别,而以和谐为纲领。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和谐”乃是最重要的社会追求[17],以致“中国所讲求的社会秩序,其重心在于‘和谐’(harmony),而不在于‘整合’(integration)”[18]。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世界本性的独特认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特征上,乃呈现出一种强调和谐与统一(unity)的“和谐化的辩证观”。[19]也正因为如此,以“稳重和平”为人格表征的薛宝钗势必会脱颖而出,成为贾母、元春、下人们的众望所归,故脂砚斋就针对“稳重和平”说:“四字评倒黛玉。”(第二十二回批语)而早在第五回,书中即借由众人之口对钗、黛取舍下了定论,所谓:“来了一个薛宝钗,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这就足以代表当时普遍的客观评价,因而脂砚斋亦批云:
此句定评,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
将这些说法比照元妃的种种作为来看,可知元春既能欣赏“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的秀异风格,却又因为“世人目中各有所取”的客观需要,而以“人多谓黛玉所不及”之“定评”作为取舍的依据,此乃着重点不同之故。
尤其当元春初见黛玉时,所见所闻的就是她种种“恃能压众,乔酸姣妒”的性格表现,一直到第二十八回借端午节赐礼而明确展示其“以薛易林”之取舍为止,这段时间都还属于林黛玉性格发展中较不成熟的前期阶段,元春并没有机会看到林黛玉性格上成熟化的转变。后期经历了成长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之后的林黛玉,虽然逐渐回归封建传统而大大趋近于宝钗[20],可惜定局已成,再也难以翻案,黛玉自己的病势更积重难返,不足以承担繁重的家务,甚至活不到举行婚礼的年纪。这或许也是一桩错失了时间点的无奈憾事。
持平而论,整个世界的运作乃是多元共生的复合模式,牵连甚广而涵盖万端,各种生命价值乃如复调(polyphony)般以同等的重要性并世共存,宝、黛爱情关系并非思考现象的唯一角度,更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判准,单单以宝、黛爱情之圆满发展为关切焦点,甚至据以强分人物优劣,毋宁是狭隘化的偏执而流于专断与排他。则明智如元春者,对二人的态度也只能说是“钗黛取舍”,而非“钗黛优劣”。既然“宝二奶奶”乃是家族社群结构中的产物,本身即是一种世俗身份与社会标签,所发挥的也是现实世界的处事功能,故舍个人取向之黛玉而取群体取向之宝钗,实有其合情切实的必然之理。王国维曾分析道:“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之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21]则元春对钗、黛取舍之结果若促进了宝、黛爱情悲剧,也一如王夫人的抄检大观园般,都是属于其中“不得不然”的第三种。
[1] 〔美〕曼素恩著,杨雅婷译:《兰闺宝录:晚明至盛清时的中国妇女》,页137。
[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上册,卷8,“选看秀女”,页149。
[3] 本书补注:“凡选宫女,于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十三以上,造册送府,奏交宫殿监督领侍等引见,入选者留宫,余令其父母择配。其留宫之女,至二十五岁遣还择配。”(清)允祹等奉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卷87,《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620册,页215。
[4] 详参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页535—536。另可参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页236。
[5]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页543。
[6] 见(清)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收入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史地类第8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页3—4,总页510—511。有关明清采选秀女之制度,详参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页116—126。
[7] (清)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收入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史地类第86册,页3,总页510。
[8]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台北:明文书局,1982),卷7,页504。
[9]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卷8,页139。
[10] (清)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1。
[11] (清)涂瀛:《红楼梦论赞·贾元春赞》,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33。
[12] (清)吴乔:《围炉诗话》,卷4,收入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99),页591。
[13] (清)陈仅:《竹林答问》,收入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页2250。
[14] (清)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211。
[15] 此段所论,参欧丽娟:《〈红楼梦〉论析——“宝”与“玉”之重迭与分化》,《国立编译馆馆刊》第28卷第1期(1999年6月),页215—220。增订版收入《红楼梦人物立体论》,页1—41。
[16] (清)涂瀛:《红楼梦论·龄官赞》,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38。
[17] 可参考黄囇莉:《人际和谐与冲突: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9)。
[18] 邹川雄:《拿捏分寸与阳奉阴违——一个中国传统社会行事逻辑的初步探索》(台北:台大社会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页133。
[19] 成中英认为,“和谐化的辩证观”乃是儒、道两家传统思考方式的代表,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时间思想及自然哲学都奠基于“和谐”此一根本价值观念;而所谓“和谐化的辩证观”即和谐化的方法论,其内涵在阐明如何化解生命不同层次所遭遇的矛盾与困难,实现生命整体与本体的和谐。参成中英:《知识与价值——和谐、真理与正义之探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序言”及页8—17。
[20] 有关林黛玉价值观的转变情形,详参欧丽娟:《林黛玉立体论——“变∕正”“我∕群”的性格转化》,《汉学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页221—252,收入《红楼梦人物立体论》,页49—118。
[2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收入王国维等:《红楼梦艺术论》,页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