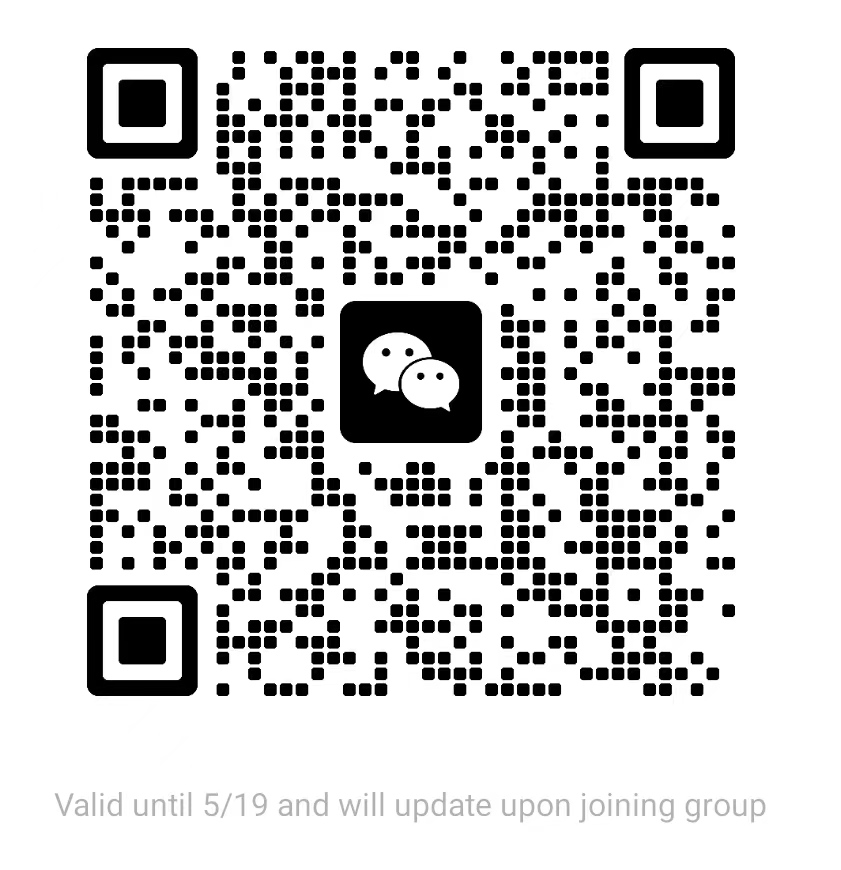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四册 >
- 第六章 薛宝琴论
五、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宝琴这位非属凡品的缥缈仙子,自难从尘土孕育的馨香中找到足以对应的代表花。若必得斟酌为之,水仙花可以算是最恰当的选择。
固然从著名的“宝琴立雪”而言,宝琴的代表花也可以是红梅花,不过,由于红梅已经明确归属于妙玉,不宜重复。此外可以注意到,与宝琴结合的花品还有腊梅与水仙,极富意味,可堪推敲。第五十二回中,大观园内的金钗们只有宝琴获得大总管赖大婶子所赠送的腊梅、水仙,当时宝玉来到潇湘馆:
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点着宣石,便极口赞:“好花!这屋子越发暖,这花香的越清香。昨日未见。”黛玉因说道:“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婶子送薛二姑娘的,两盆腊梅,两盆水仙。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蕉丫头一盆腊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负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转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
这是整部小说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涉及宝琴与花卉的情节。应该分辨的是,腊梅原作“蜡梅”,并不是梅花,不仅花期较早,以黄花为主,花香更是浓郁,与梅花的五颜六色、淡淡暗香不同。虽然宝琴获赠了两种花品,也各自分送一盆给黛玉、探春,但一则是受礼者已经都个别拥有芙蓉、红杏为代表花,此处的转赠与此无关;再则是这段情节所聚焦描绘者只在于水仙,蜡梅只是附带提到,自以水仙为主。水仙花亭亭玉立于水、石间,水清玉洁、不染尘土,在暖阁温室里安适地散发清香,与户外植根于淤泥中、承受着风霜雨露的水莲大为不同,最和送花人的气韵互为一致。毋怪乎此花以“仙”为名,即挑明了宝琴的浑身仙气。
更何况再细细加以揣摩,宝玉所极口称赞的“好花”,岂非正对应于宝玉在初次见识了宝琴之后,所赞叹的:“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而宝玉所说的“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又恰恰是宝玉初见宝琴之后所感叹的:“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意同于探春所认证的“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如此一来,这盆水仙花便可以说是宝琴的化身,让其他群芳相形见绌,故得以代表花视之。
值得思考的是,当所有的金钗都各有长短的时候,宝琴则因为没有“陋处”“纰漏处”而“品格似出诸美之上”,一如仙界的女神兼美是“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第五回),薛宝琴正可谓“世间的兼美”,这或许也是她给予人不带烟火、完美却不真实之感的深层原因。
到了贾家后,宝琴一直没有涉入府中的任何事务,接下来无论是探春轰轰烈烈的兴革整顿,王夫人的抄检大观园,都不见其踪迹,更不发一词。探究起来,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三:
第一,身为即将发嫁、暂住于此的远客,正如凤姐评论宝钗、黛玉时所说的“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第五十五回),这是疏不间亲的普遍原则所致。
第二,宝琴伴随贾母起居,享有治外特权,生活上也远离大观园与荣府的日常运作,不比宝钗仍然住在大观园里,多少涉及园中所发生的人事纷争,也有避嫌的思虑,此乃宝琴的特殊处境所致。
第三,除小说内部的人情事理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因素是来自小说家的刻意为之,即为了保持宝琴不染人间烟火的脱俗形象,势必要尽量削减种种人事牵连,于是宝琴便始终以局外人的姿态活动着,于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二回的绚烂现身之后,乃化身为点水蜻蜓,若隐若现。对于宝琴何时离开贾府,小说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并且以她深受贾母宠爱的程度,她的离开势必有一番场面,但事实上却是悄无声息,这应该也是来自《红楼梦》未完的遗憾。
从前八十回的线索可知,宝琴因名花有主,而无缘于宝玉的金玉良姻,第四十九回交代宝琴之所入京的缘由,乃因“薛蟠之从弟薛蝌,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正欲进京发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第五十回透过薛姨妈之口,再度强调她父亲“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则宝琴最后应该是顺利发嫁,进入梅家为媳。参照第七十回放风筝一段情节中,宝琴的风筝造型是“大红蝙蝠”,犹如怡红院里四面雕空玲珑木板上亦有的“流云百蝠”(第十七回),以传统文化的符号象征意涵而言,蝙蝠的“蝠”谐音“福”字,乃吉祥之化身,再加上喜气洋溢的红色,可以推测宝琴的婚后生活将一如在室时期的幸福圆满。
只不过,既然诸钗都隶属于太虚幻境的薄命司中,宝琴理应不能单独例外,何况众人一起作《柳絮词》时,宝琴的《西江月》也同样融入大观园的悲凉之雾,充满离恨丧败之哀音,所谓“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偏是离人恨重”,在汉苑、隋堤的怀古声调下,流淌的是幻灭离散的哀音,与大观园中的伤悼氛围相一致。其中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宝玉曾断言《桃花行》必定不是出于宝琴之手,原因是:
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第七十回)
亦即宝琴之诗才自能作出《桃花行》之类的诗篇,但在诗谶的顾虑下必须趋吉避凶,宝钗出于爱护堂妹之心,绝不许宝琴操觚哀吟;宝琴一生幸福顺遂,自己更没有无病呻吟的必要,故不为也,因此宝玉的断言才会如此斩钉截铁,也确实道中黛玉乃真正的作者。
然而,宝琴的《西江月》确实落入离恨丧败之窠臼,因此宝钗紧接着以翻案手法写出明朗乐观、积极向上的《临江仙》,以力求扭转集体的悲剧情调,可见宝琴对这类的感伤风格是既能也,亦为也,并非宝玉所推论的“断不肯作”。如此一来,便透露出宝琴并非纯然无忧无虑的世外仙子,以其聪敏灵慧遍历大江南北,触目所及绝不只是繁华富庶、歌舞升平,对于人世间的无常飘零自有一番会心。何况触发怀古诗的古迹,本身即蕴含了古今沧桑的感慨,而怀古心灵“所关怀与反省的,不仅是个人生命的存在,乃是众人共同的命运,是社会的也是自然律的生命的困境”,因此怀古诗所表达的是生命无常的历史悲感,故带有对整体的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1],则写作怀古诗的宝琴,又岂能无感于沧桑的悲慨?
参照海外真真国的外族美人所作的五律诗中,第一句“昨夜朱楼梦”的“朱楼梦”即“红楼梦”,却已是次日的残像虚影,宝琴自己的“明月梅花一梦”何尝不是如此?在“月本无今古”的对照之下,“情缘自浅深”的人们又饱受多少无常磨折,宝琴对此怎会没有触动?大观园的“红楼梦”势必随她离府出嫁而告终,婚嫁后的“明月梅花一梦”也似乎隐隐然蒙上了幻灭的阴影,情深、情浅都终归空无。只是毕竟小说家没有完成宝琴的未来,只能存而不论,宝琴的形象便始终停留在姑射山上的白雪红梅里。
也因此,宝琴的人物形象中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她几乎没有喜怒哀乐之类的情绪表现。整体来看,宝琴除有“心热”的亲近友爱之外,仅有一次被揭发谎言时的尴尬脸红,低头微笑不语,除此之外,对于宝琴的人物呈现,小说家完全没有涉及凡人喜怒哀乐爱恶欲的种种情绪,也就是没有写出她的内心世界,相较于其他所有人物,诚属非比寻常的特殊现象。姑且不论多愁善感的黛玉几乎时时都在绽露自己的情绪,连探春、湘云、迎春、惜春等也处在各自的烦难冲突中,而难免痛苦与眼泪;即使槁木死灰的李纨尚且出现与凤姐交手争锋的狂飙,以及对妙玉矜傲逸轨的不满,甚至“皮里阳秋”的宝钗都还有唯一的一次伤心、唯一的一次愤怒、唯一的一次嫉妒,但对比之下,宝琴则毫无情绪波澜,其内心之幽密更加难以一窥,因此其“真精神”便缺乏令人印象深刻之处。
无论这是因为众美皆出、难有超越的困境,导致小说家只能用一种抽象的笔墨给予强调,成为一抹缺乏血肉的优美影子;还是另有小说美学突破的匠心在焉,企图超越“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的规范,以至于即使没有陋处更构成了真正美人,总而言之,宝琴的人物塑造充满与众不同的手法,调动了绝无仅有的情理逻辑与现实因素,足以在令人目不暇给的人物长廊中一枝独秀。犹如宝玉见了宝琴等人后的极端赞叹:
你们还不快看人去!……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瞧他这妹子,更有大嫂嫂这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
不仅宝玉增长了见识,坦然承认自己是井底之蛙,连贾母是见过大世面的老封君,数十年来识人无数,却一见宝琴便动心改念,可以说,曹雪芹借口由宝琴的出场,实实在在地告诉读者:这世界上还有比宝钗、黛玉更出色的人,读者因为不在叙事现场,也因为各有所好,固然不必因此而改变既有的喜爱对象,但在人性的理解、审美的多元上,若是顽强地偏执于某一特定的人物,那就是画地自限;若是因为此一偏执而否定、排斥其他不同的人格境界或生命姿彩,那更是自我耽误,有如理性能力不足的幼稚孩童,或者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深刻洞彻到人性的一个弱点,指出:
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儿的、乡下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2]
连“成日家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宝玉都坦然自承“井底之蛙”,遑论其他?若要不落入小心眼儿的、乡下佬式的思考和判断,始终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缩小自己,不把自己看得太该死的重要,所谓:
人不能狂妄自负地听从自己。他必须使自己沉默,以便去倾听一个更高和更真的声音。[3]
空出心胸来容纳无比宏大的世界,这是提升自己的唯一方法。
[1] 廖蔚卿:《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大主题:从〈登楼赋〉与〈芜城赋〉探讨远望当归与登临怀古》,《幼狮学志》第十七卷第三期(1983年5月),页104。后收入廖蔚卿:《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7),页72─74。
[2]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一章“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页21。
[3]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一章“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