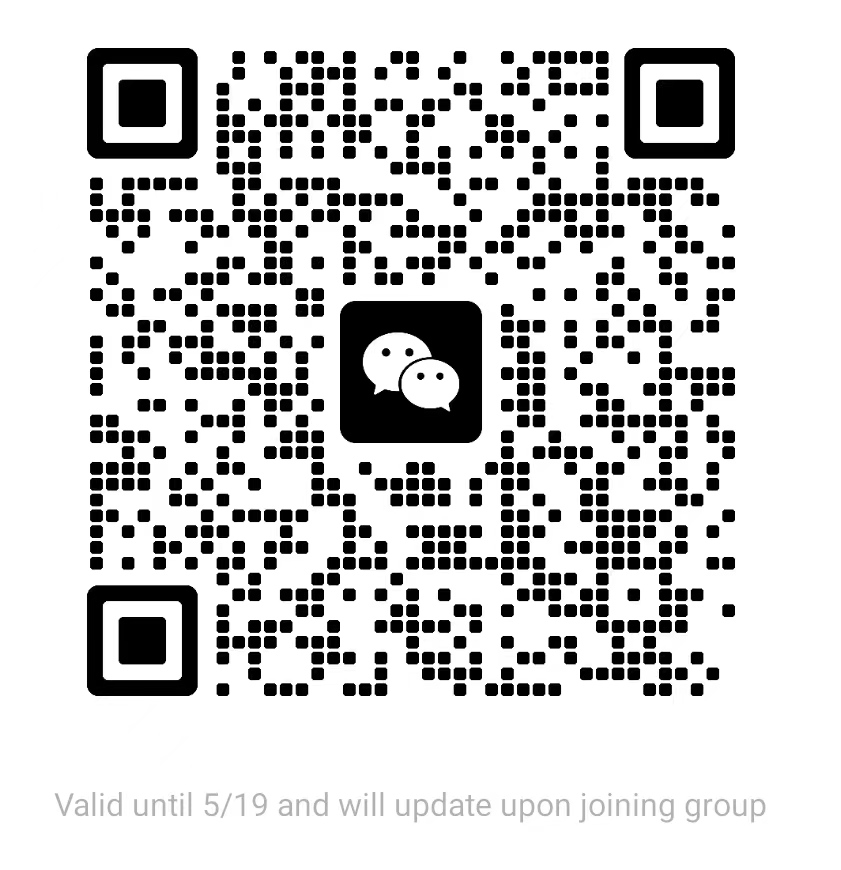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三册 >
- 第六章 贾探春论
二、大观精神:宰相器识
(一)秋爽斋的人格化身
秋爽斋是探春迁入大观园之后的住处,人、屋合而为一,其中的布置与各种摆设都显示出屋主的性格内涵。第四十回描述道: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
烟霞闲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
从整体的格局摆设,在在展现出一种恢弘阔大的气度,除利用“大理石大案”“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大鼎”“一个大观窑的大盘”“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等各式用品,一连以八个“大”字为描述关键字(包括大理石、大观等专有术语),更包括房内东边所设的拔步床。作为一种有着立柱、横架、隔窗、顶篷、平台等的大型卧榻,拔步床不同于怡红院中那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的“小小一张填漆床”(第二十六回),也摆不下“小小两三间房舍,一明两暗”(第十七回)的潇湘馆,只有秋爽斋将三开间都打通的格局才不会显得局促,而恰如其分。
可以说,秋爽斋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就已经展现出开阔恢弘、坦荡磊落的大器风范,那整一宽敞的通透自如正是探春“素喜阔朗”之心胸的具体化。衡诸贾府的三春众芳,其中唯有探春能如湘云般同为一股清流,以明爽豁朗之气洗污去浊,没有心理的曲折失衡乃至阴暗扭曲,因此既无机关算计更无不可告人的隐衷,脂砚斋便说道:
湘云探春二卿,正事无不可对人言芳性。(第二十二回眉批)
这种“事无不可对人言”之“芳性”,所表现的性格特质之一便是诚实不伪,第四十九回邢岫烟、李纹、李绮、薛宝琴四人结伴来到贾府,薛宝琴尤其受到贾母赏爱,探春转述道:
“老太太一见了,喜欢的无可不可,已经逼着太太认了干女儿了。老太太要养活,才刚已经定了。”宝玉喜的忙问:“这果然的?”探春道:“我几时说过谎!”
探春确实从不说谎,但她与湘云仍然同中有异。比较起来,湘云的“英豪阔大宽 宏量,……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 ”(第五回)主要是来自天赋自然,因此颇有一种不假雕琢的率性;探春则是源于一种自觉的人格追求,因此处处于日常中实践,成为一种具有鲜明表征的生活模式。
试看那一大幅“烟雨图”“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以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可见其超逸自在、不求闻达的淡泊性格,连床上所悬挂的都是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据板儿的指认,上面点缀的草虫包括蝈蝈、蚂蚱在内,竟有一种来自土壤的清新韵味,和可卿的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第五回)、宝玉的大红销金撒花帐子(第二十六回)、宝钗的青纱帐幔与水墨字画白绫帐子(第四十回)都大异其趣。而从“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又可知她追企古人而勤于摹效的敬谨向学之心;再看大盘中所盛的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日后将成为联系巧姐与板儿之姻缘的凭借 [9] ,则可见她温情慈善的柔软心怀,于是成为慈悲引渡之潜在场域;至于洋漆架上所悬的一个白玉比目磬,以及旁边所挂的小锤,则呈现出探春严谨有度、知法守理的另一面性格。可以说,恢弘坦荡的秋爽斋整体上有类乎宰相器识,探春则是庙堂之上的大雅君子。
只是在整部小说中,探春的人格表现大致是以第五十五回为界分,在第五十五回受命理家前,属于怀才不遇、韬光养晦的沉潜阶段,但她甘于恬淡,优游于个人生活中怡然自得,一无怨天尤人的穷酸气,还充分品尝各种清新自然、优雅精美等同归于脱俗的不同品味。例如第二十七回探春对宝玉笑道:
“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侯,或是好字画,好轻巧顽意 儿 ,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这些。怎么像你上回买 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 么似的 ,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五百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一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 者,这些东西,你多多的替我带了来。”
可见探春对一般人所喜欢的绸缎、吃食、衣服毫无兴趣,除了体现人文精神气韵的好字画之外,还欣赏那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清新事物——所谓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都是在自然之物上添加巧思,成本低廉、甚至不用成本的小巧玩意,因而没有人工经营的匠气,却又充满创意。并且,她是唯一将审美趣味延伸到贾府以外的人,因此也是唯一主动拜托出得了大门的宝玉,去替她带回这些东西的金钗,那不甘为闺阁所限的性格,已呼之欲出。
再者,第三十七回袭人回到怡红院准备拿碟子盛东西,却发现碟槽空着,于是问道:
“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去了?”众人见问,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巴巴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尝不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叫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
鲜荔枝是红艳饱满的,诗中多所赞颂,如唐代诗人戴叔伦《荔枝》的“红颗真珠诚可爱”、郑谷《荔枝》的“晚夺红霞色”,白居易《题郡中荔枝诗十八韵兼寄万州杨八使君》一诗更是连续以“丹实夏煌煌”“深于红踯躅”“燕支掌中颗”等等渲染其艳丽色泽,放在白玛瑙碟中,红白相映、晶莹剔透,极其赏心悦目,显出在平凡生活中处处发现美的灵心慧眼。平民出身的袭人、晴雯自不能领略这分美感意趣,宝玉与探春这对贵族兄妹则心有灵犀,一个在送去时费心组合,一个则留下细心赏玩,这种有别于“朴而不俗、直而不拙 ”的精致娇艳、清丽脱俗,同样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审美眼光,与高超的艺术修养。
无怪乎,探春是诗社的第一个发起人,号召姊妹们的文书中除典雅的古文之外,还兼用中国传统文学中最精致的骈文,如专函递送给宝玉的花笺上写道:
娣探谨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之下,未防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昨蒙亲劳抚嘱,复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痌 惠爱之深哉!今因伏几凭床处默之时,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娣虽不才,窃同叨栖处于泉石之间,而兼慕薛林之技。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则扫花以待,此谨奉。(第三十七回)
宝玉看了,不觉喜得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的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探春不仅一招皆到,立竿见影,而且剑及履及,当下便订定完善的社规并开咏海棠诗,从成立到运作一气呵成,既开先锋又立下良好的基础。探春游心诗词的雅兴、推动事务的才干,都由此可见。
同时,花笺中所提到的“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讵忍就卧。时漏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槛之下”,正透显出探春赏爱自然清景的襟怀与生活情韵,竟可以为了珍惜如洗的月色而徘徊流连直到中宵,遥承苏轼《记承天夜游》的“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10] ,大大有别于黛玉的流泪到半夜,以及宝钗的灯下女工常至三更,那月光所勾勒的身影绝非柔弱、娴静的一般闺秀,只有高旷清朗的雅士足以当之。如此种种,与王羲之于兰亭曲水流觞、挥毫写序,以及苏轼月色下欣然夜游的风雅岂非同一心源?正符合其生日所隐含的象征意义之一,而探春正是大观园中的王羲之与苏东坡。
并且,这些情节都出现在第五十五回受命理家前怀才不遇、韬光养晦的沉潜阶段,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安于隐逸、自得其乐,处处展现脱俗的审美意趣、高洁的人格操守,以及理性清明的眼光,这就是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志”的展现。证诸明代洪应明所言:
思入世而有为者,须先领得世外风光,否则无以脱垢浊之尘缘;思出世而无染者,须先谙尽世中滋味,否则无以持空寂之苦趣。 [11]
可见探春的性格不只是一般但求快意自适的文人逸士,还更是无入而不自得的大雅君子,既能积极入世,谙尽世中滋味却脱垢浊之尘缘;又能退隐山林,领得世外风光而持清空之逸趣,可谓进退皆宜、动静自如,实为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的君子典范。
(二)法理的客观精神
大雅君子必是有为有守,沉潜时独善其身,守其朴真、为其所乐;得志时则兼善天下,守其节度、为其所能,探春便是如此。特别是在第五十五回的“用行”阶段开始后,探春这一方面的性格特质更充分地显现出来,如烟火般绚丽夺目;然而,即使还在“舍藏”的早先时期,这分注重法理分寸的精神仍然表现在生活的细节里,秋爽斋中洋漆架上所悬的一个白玉比目磬,以及旁边所挂的小锤,便是用以象征探春严谨有度、知法守理的另一面性格。
此乃因磬者,作为法器或乐器,无论是报时或度曲,其共同性都是展现一种客观公正的权威,代表了律令、法度、法统、规范、分寸等不可违乱之行为准则,但玉之温柔润泽又适度软化其刚硬严峻;相对而言,其锤之“小”对反于其他摆设之“大”字,则是隐喻其谨守分寸的安分克己,当握有权力、大刀阔斧之际,也是不多走一步失了本分,不少做一分失了责任,绝不失于王熙凤的“逸才逾蹈”(第五十六回脂批),落入滥权渎职的局面。
其次,细察整个大观园中,也只有探春的秋爽斋附设了一处独立的、公共用途的“晓翠堂”,以供群体活动之用,其他姊妹们则多如贾母所说的:
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怕脏了屋子,……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玉儿可恶。(第四十回)
可见探春也是能够与人和谐共处,具有合群的能力,这却又无碍于“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之潇洒恬淡,以及芭蕉、梧桐般卓尔不群之高洁脱俗。可见探春是一个公私平衡的人物,达到人生涵盖面的扩大与完整,既安顿了自我,也安顿了周遭群体,将“大观园”实践为“大观世界”,而绝佳地体现了在自我认定性中所具有的“社会特性与个体特性紧密交织”的双重性,故能施展出整顿大观园的兴利除弊之举,这或许就是探春合乎“大观”精神之所在。
此所以在大观园的世界里,除了这座园子本身、元妃省亲时所驻跸的正楼被赐名为“大观园”“大观楼”,此外,唯一在命名上拥有“大观”之称者,则仅见于探春房中一系列以“大”字为共通符号的各式摆设之一的“大观窑”。其屋内各式用品一连以八个“大”字为描述关键字,既与“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的阔朗格局一样,都是用以彰显一种开阔恢弘、坦荡磊落的大器风范,却也是顺势带出“大观”一词的绝妙修辞策略。若仔细比较,获取小说家以“大观”一词为描述者,不见于贾宝玉那精美绝伦仿若迷宫的怡红院,也未施诸林黛玉犹如上等书房的潇湘馆,以及薛宝钗如雪洞般的蘅芜苑,却单独用在探春的秋爽斋中,这岂非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尤其是根据考证,虽然清人的“大观窑”其实就是古籍中一贯说的宋代官窑而已, [12] 但既然在清代陶瓷专书中,“大观窑”往往被联系到宋徽宗的“大观”年号为说,如《南窑笔记》载:“出杭州凤凰山下,宋大观年间命阉官专督,故名内修司。……为宋明十大名窑。”《景德镇陶录》亦指出:“大观,北宋年号。”则《红楼梦》之取材于“大观窑”,仍是透过宋徽宗的“大观”年号而承继了传统的政治意涵,通过窑名而与园名、楼名一致,隐隐然亦有借探春以彰显大观精神之意。
据此,则探春似乎被视为大观园中唯一真正具有“大观”之实者,并证成了何以“玉原非大观者”(第十九回脂批)的真正意涵,实为发人深省。换句话说,当第十七回宝玉在抗议稻香村“似非大观”之际,即已暴露其偏泥一端的局限,以如此“原非大观者”的局限性,宝玉在探春管家之后屡屡表现出的异议,不仅不是小说家的批判,实则适得其反,是用来加强宝玉的自私与不肖。例如第六十二回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看探春理事,黛玉便说道:
“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钗说笑去了。
可见连黛玉都已经看出家庭的严重问题,宝玉却一味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参照第七十一回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显示出只顾眼前享乐而从不忧心后患的短视,以及对“覆巢之下无完卵”之理的无知;只要自己和黛玉的所得不会短缺,别人的短缺乃至整个家族的窘困都不放在心上,这种心态更流于自私自利。探春身为致力回天的孤臣孽子,既忧心家族的存亡兴衰,更尽其所能地深谋远虑,必然只能做一个“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何况连世外仙姝的黛玉也都“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了,宝玉这个更应肩负责任的继承人不仅推卸责任,还对苦心补天、让他得以一味无知自私的人妄加批评,只是自曝其短而已。小说家在此安排了二玉的分歧,正隐含了谴责宝玉的弦外之音。
至于黛玉对探春所形容的“乖人”,有人据传统文献而整理出三种含义,一是“离人”,如刘桢《赠徐幹》的“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二是机灵、乖巧之人,见《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三是奸滑之人,如李渔《奈何天·闹封》中的“笑乖人,枉自用心机”,并认为黛玉所言,兼含前两者之意,而归结为“处世能手”。 [13] 实则黛玉当时的语境中,不可能有“离人”之意;至于机灵、乖巧之“处世能手”,不仅不切合探春的性格特质,也不符合黛玉的上下文用法。
推敲黛玉与宝玉对话的整个语脉,应该说,黛玉所谓的“乖人”,其实指的是谨守原则分寸,不逾矩、不滥权,所以下面才会说“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接着所说的“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则是在同意“乖人”的描述与判断后的进一步补充,指出在“乖”之外的另一面,也就是探春固然“一步儿不肯多走”,却绝不只是墨守成规,而是在算计之下还动手改革,展现出积极进取的作为。换言之,黛玉所说的“乖人”是赞美探春掌权后“有守”的一面,因此没有得意忘形、作威作福;宝玉则是从自己权利受损的角度批评探春“有为”的一面,这正是“有为有守”的另一种说法。
可以说,宝玉一心陷溺于主观私情,故被贬为“原非大观”;探春则公私兼具,并且在维系纲纪秩序的补天过程中,往往以客观法理凌驾于主观私情,表现出真正的大观精神。进一步来看,在小说中,探春也属于“受得富贵,耐得贫贱”,也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一位高格女子,但与同样达到此一境界的宝钗又有所不同。宋代的洪迈曾指出:
妇人女子,娩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 [14]
以此为标准,探春正是不折不扣的“烈丈夫”,绝非娩娈闺房的妇人女子;相较之下,宝钗固然没有一般妇人“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的软弱无知、情绪化反应,也达到“以智决策,斡旋大事”的品识高度,但毕竟主要还是“以柔顺静专为德”,由此也注定了“以义断恩”的缺乏。
探春则不然,粗略地说,不同于黛玉的个人主义、宝钗的人文主义、凤姐的现实主义,探春是《红楼梦》中唯一的理性主义者。而理性主义追求的是客观公正,因此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处事以“法理”为优先。“法理”是超越人性偏私的社会准绳,先秦慎子云:
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15]
汉文帝时任廷尉的张释之也说道: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16]
只可惜,探春生于极端重视人情的中国传统社会,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大众往往因此而徇私徇情,导致是非不分,读小说时更是只求感觉的满足,以致清代评点家即认为:“《红楼梦》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红楼梦》可不作矣。” [17] 但这其实是在常识层面下的偏颇之见。《红楼梦》固然是“大旨言情”,但所言之情绝不限于儿女私情,更多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各种感情;并且更正确地说,即使涉及儿女私情,若不在法理的限度内以达到情、理兼备,该儿女私情也是受到谴责与罪惩。其中,探春的法理优先可以说是小说家对于女丈夫的绝大颂扬,唯一给予“大观”之名便是清楚的证明之一。
就这一点而言,探春最具有代表性的作为,是在抗拒生母赵姨娘的血缘勒索时,对宗法制度的坚持上,请见下文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