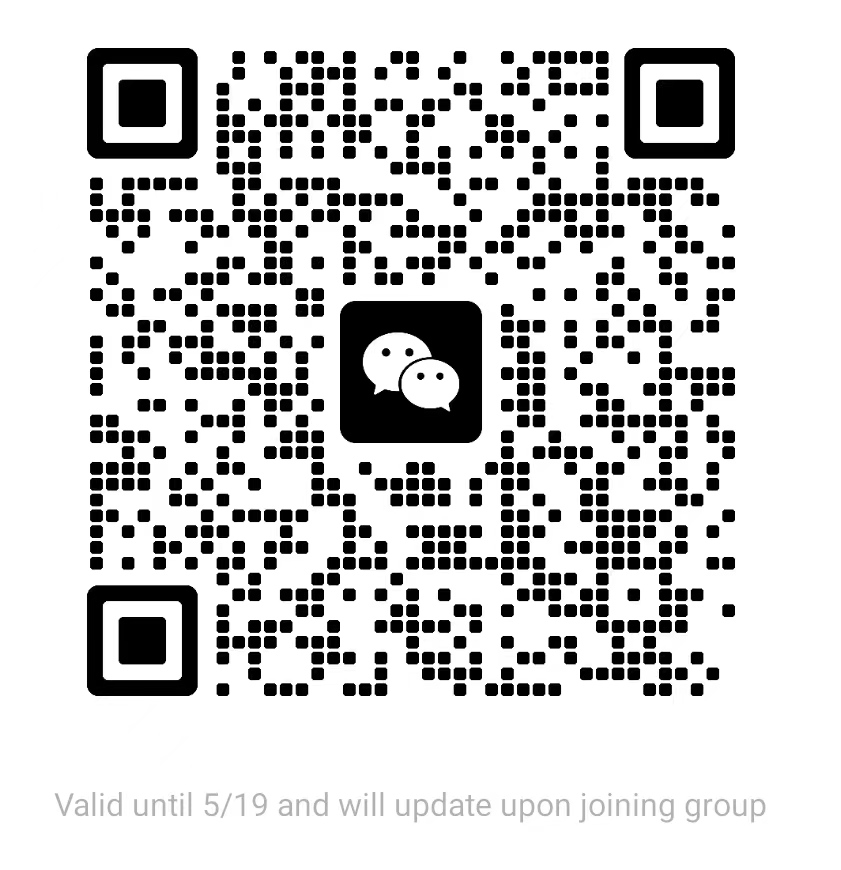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三册 >
- 第五章 薛宝钗论
二、成长背景与人格特质
(一)皇商的家世环境
元月二十一日,宝钗诞生于诗书世家兼皇商的簪缨之族。 [14] 而这是一个与贾府大同小异的家庭:
大同者,即薛家事实上“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第四回),“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 ”(第四十二回),都属于诗书名门,具有世代门风,绝非西门庆之类的暴发户。金陵地区所流传的护官符中,对薛家的说明乃是: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第四回)
一般人只注意到“珍珠如土金如铁”的“富”的一面,却忽略了“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的“贵”的一面。薛家先祖所担任的紫薇舍人,即中书舍人,专职撰拟诰敕之责,有文学资望者始能充任,地位崇高;因唐玄宗开元六年将中书省改为紫薇省,中书令为紫薇令,故有此一别称。白居易担任中书舍人时,作有《直中书省(一作紫薇花)》一诗云:“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丝纶阁即草拟皇帝诏书敕命的地方,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自称紫薇郎,正是此一历史典故的实证。薛家先祖担任中书舍人而称为“薛公”,与其名望地位相符,由此乃与国勋门第的贾府并列为四大家族。
小异者,即薛家以皇商、行商的身分从事买卖营生,与贾府是国公世袭的勋爵,主要财源来自庄田之农牧生产有所不同。参照第七十九回贾赦作主将迎春许婚于孙绍祖时,贾政不表赞同并且一再劝谏的理由,正是孙家“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清楚可见“诗礼名族”的家世条件才是薛家得与贾府联姻,且并列四大家族的原因,也是理解薛宝钗至关紧要的关键。既然“书香继世之家 ”才是贾、薛两家的大同之处,“皇商”则仅是小异之别,则一般只就“皇商”以偏概全,又脱离清代的历史背景,从世俗常识下的“商人”特质对宝钗作扩张性的解释,那便几乎注定了歧路亡羊。
除护官符所说的“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当宝钗第一次出场时,小说家即对其家世给予大致完备的交代,第四回大篇幅地描述道:
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 。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其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
于是宝钗便随母兄一起来到贾府。其中,“皇商”绝非社会上的一般商人,而是上通皇室、遍及全国乃至近海的超级企业家,为“行商”中势力最大的魁首 [15] ,除户部挂名之外,还包括“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 ”,其具体项目至少有木店(第十三回)、当铺(第五十七回)、常和参行交易的铺子(第七十七回)等各铺面(第四十八回)。因此宝钗的堂妹宝琴,同为薛氏女儿,其父亲也是“各处因有买卖,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第五十回),甚至扩及海外,如宝琴自述“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于是亲眼见过“海外真真国”的十五岁女孩子(第五十二回),其贸易范围之广、所见世面之大,一如与之联姻的王家。参照第十六回王熙凤所言:“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可见王、薛两家都拥有远洋贸易的家族事业,更是门当户对。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回赵嬷嬷提到多年前康熙南巡时,“咱们 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 ,只预备接驾一次”,则贾府先前的职任也曾涉及造船、筑港之类的海洋事业,这应该是与薛家、王家发生互动,形成世交亲家的机缘所在。如此一来,贾、薛两家的“小异”之别,恐怕其差异还要更小。
除名列“护官符”上四大家族的王家之外,薛家的其他联姻对象也同样具有类似条件,薛蟠后来所娶的正室夏金桂便属同类。第七十九回经由香菱的描述,指出:“这门亲原是老亲,且 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 。前日说起来,你们两 府都也知道的。合长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 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因此才有这个 浑号。 ”因为门当户对,于是在薛蟠的苦求之下,薛姨妈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并且,之后因为夏金桂的泼悍无礼而产生婆媳冲突时,薛姨妈气得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 儿 !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些什么!”(第八十回)所谓“旧家人家”,正近乎贾家“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第十三回),“旧”字都说明了历史悠久的家世传统,这才是构成相关家族的完整条件。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薛家这些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贸易中,包括了被严重污名化的当铺。第五十七回,岫烟被婶母邢夫人与下人们欺榨,不得不典当绵衣以应付需索时,补述薛家也经营了当铺:
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
就这一项家业而言,一般的直觉反应都是负面的,尤其是第五十七回湘云捡到当票并了解其意涵后,与黛玉二人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似乎更证实了这是一门“太会想钱”的黑暗行当。于是对薛氏一家怀有敌意的读者便借题发挥,丑化宝钗的人格。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其主体能动性,所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不仅才性能力无法遗传,一个人的品格是否能直接等于他的家庭,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哉问,其复杂性牵涉万端,毫不考虑各种情况便一概混同为说,更属于成见与谣言的层次,不足为训;并且经营当铺是否便属于非法悖德的不良事业,也还是一个应该确认的前提,不能以粗略的直觉想当然尔。事实上,从《红楼梦》所奠基的清代旗人文化,以及与皇室密切相关的历史背景而言,薛家的当铺完全是合法的营生项目,并且与皇家及其所属的内务府有关。
历史学的研究指出:“由于清朝禁止皇族及八旗兵丁经营工商业,所以皇族经商记录并不多见,从档案中看到他们在清代初期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当铺、钱庄。……清代皇帝的内务府开设当铺,在公主下嫁或皇子分府时赏给当铺,如荣安固伦公主下嫁时恩赏当铺一座,每月房租银一百三十两。庄静固伦公主出嫁时恩赏克勤当铺一座” [16] ,可见当铺、钱庄的经营本就是皇族主要的商业活动,甚至成为公主的嫁妆,非但不是邪恶的行当,反倒是光明正大、显贵尊荣的。同时不仅皇帝的内务府开设当铺,内务府的包衣旗人若积存不少财产,也会以变通的方式,“暗地里出资本,请汉族人领东,经营商业。内务府人员出资所经营的商业,主要是两种买卖:一是古玩铺,二是当铺”。 [17] 则不仅曹雪芹以其自家的内务府包衣家世,应对当铺的经营十分熟悉,移植到小说中的薛家,也符合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的背景。足见当铺不仅合法,并且是具有相当资产身分的显荣之业,绝不能以市井泼皮“醉金刚”倪二的放高利贷相提并论。
除清代历史背景下的“合法性”之外,也许还可以思考的是,当铺的存在是否有其“合理性”乃至“合情性”?从本质上来看,在“万法唯识”的东方哲学里,世间万事的意义往往存乎一心,同一件事的做法会因人而异,由此也决定了成败与价值。只要不心存成见,便可以思考:当铺的存在是因社会需要而生,无论贵贱贫富,当财务上出现一时窘迫所产生的金钱缺口,却又求助无门的时候,除非将有价物品直接变卖换取现金,否则当铺便是需钱孔急时唯一的救星。所谓“一文钱逼死好汉”,这种末路绝境非亲身经历者不易体悟,然则钱从何处来?世间本无天上掉下银钱的道理,一旦面临山穷水尽之苦,若无亲朋好友慷慨解囊,又欠缺巧遇慈善家的运气,此际便只能向陌生人求助;但陌生人非亲非故,彼此没有情感与信赖的基础,如何可能无条件地以钱相予?并且既然奉茶赈粮、济衣盖屋、铺桥造路等物资的免费提供都已属于慈善的极致,更如何可能要求当铺以超越慈善的极致而直接奉送银两?只要设身处地,便知实为强人所难。即使不将本求利,也至少必须避免亏损,足以维持各种营运,因此,当铺付出银两给上门的陌生人时要以等值物品作为担保,堪称无可厚非,不仅合乎情理,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的好意——它提供一个让人们继续保有重要物品、无须彻底割舍的希望与机会,所收取的利息实为合理而必须的报酬,是求助者应有的相对的回馈。一味抨击当铺的存在与意义,其实是出于局外人的主观愿望与偏颇认知,并不符合理性客观的要求。
因此,重新评估湘云与黛玉二人并在场众人所批评的“人也太会想钱了”“天下老鸹一般黑”的那一段对话,并不是完全公平的评论。湘云、黛玉二人出身于对经济事务、财务难关一无所知的深宅大院,完全缺乏社会经验,属于厨娘柳家的所说的:“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第六十一回)这样的千金小姐如何能感受到几文钱所带来的艰难?尤其在不问世事的诗书教养下,难免只要涉及金钱便觉得庸俗,故她们的感叹乃是来自出身背景的自然反应;而婆子们身为奴仆之流的底层人员,出入市井之间,乐于赌钱吃酒,所接触者应是泼皮“醉金刚”倪二之类,所言自属“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五十六回)的市俗之见。若读者引述这段话以批评薛家,便不自觉地陷入“何不食肉糜”的错误思维。
换句话说,当铺本身是因应社会需要而形成的急难机构,只有在不肖业者收高利贷的情况下才算是趁人之危的吸血鬼,否则便可以成为救助急难的“类慈善团体”。而薛家的营运方式是哪一种呢?小说文本中并没有具体描绘,但若推敲“恒舒典”的铺名,字面上是“永远舒缓、总是舒坦”之义,已经隐隐然意味着至少在经营理念上是救助急难的,那上门求助的邢岫烟,岂不正是在孤立无援之中借以度过难关的一个具体案例?比起自家姑母邢夫人的苛扣、刁奴恶仆的欺榨,迫使无依弱女不得不走上典当之途,“恒舒典”适时伸出援手给予纾困,岂非仁慈得多?若再参照薛家的阶级特性、宝钗的家庭教育及其人品,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薛家当铺的营运方式应该是“类慈善团体”的这一种。
最重要的是,一般很容易忽略薛家事实上也“本是书香继世之家 ”,犹如杨懋建所注意到的,与《金瓶梅》“极力摹 绘市井小人 ”迥然不同的是,《红楼梦》一反其意而“极力摹绘阀阅大家 ” [18] ,笔下展演的“阀阅大家 ”,即包括:贾府为“世代诗书 ”(第十八回)、“代代读书 ”(第十九回)、“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 ”(第六十六回)的“诗书旧族 ”(第十三回)、“诗礼簪缨之族 ”(第一回)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 ”(第二回),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 业经五世,……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第二回)、“世代书宦之家 ”(第五十七回),李纨系“金陵名宦之女,……族中男女无有不 诵诗读书者 ”(第四回),王熙凤属“诗书大宦名门之家 ”(第四十五回);至于其他与贾府无姻亲关系者,包括妙玉“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 ”(第十八回),故有贾母断言“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 ”(第五十四回)的原则性推论。这才是理解薛家最切要的一个角度。
这类诗书与富贵相结合的书香世家(family with a literary reputation),提供了优良的教育资源,以及对心性气质的高雅熏陶。先就“读书学识”而言,既然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而实际上人格的培养又在于学问 [19] ,同样地,薛父因“酷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第四回),于是对于人格产生了高度的陶冶,小说中所聚焦而不断出现的贾、史、王、薛、李、林等重要人物,也都不外乎此,宝钗能说出“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第五十六回)的深刻体悟,更是其中最了解、也最受益于学问力量的一位女性。因此,一般以商人(即使是儒商)精神解释宝钗的性格内涵,其实是缘木求鱼。
但薛家就和贾府一样,都处在没落的最后阶段,宝钗的成长与转变也与此一过程有所关联。
(二)成长过程及转变
得天独厚的宝钗拥有与生俱来健康的体质与健全的家庭,这些都帮助她在各方面出类拔萃,展现出优雅美丽的非凡容态。小说家对宝钗描写,包括:“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 ”(第四回)、“容貌丰美 ”(第五回)、“肌肤丰泽 ”(第二十八回),都与黛玉形成不同的对比,小说中也多处就此一差异加以突显,例如:
宝玉在太虚幻境所遇到的女神兼美,其所兼之美,即包括“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 ,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可见“鲜艳妩媚 ”和“风流袅娜”是不同的美感类型,宝钗的“鲜艳妩媚”,具体地表现在“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第八回),恰恰与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第三回)形成复制翻版的孪生品;至于体态上,宝玉的“越发发福”(第二十九回),也与宝钗的“体丰怯热”“他们拿姐姐比杨妃”(第三十回)相近,因此成为彼此的显性重象。再者,透过宝玉的眼光,宝钗之美比黛玉另具一种吸引力,所谓:
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正是恨没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第二十八回)
这种莹润细腻、肌肤丰泽的美感,便透过“雪”的意象加以具体化。早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已将宝钗之重像杨贵妃形容为“雪肤花貌参差是”,此一“雪肤花貌”也移到了宝钗身上,第六十五回中,兴儿对尤二姐描述家中的年轻女眷时说道:
我们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两个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姓薛,叫什么宝钗,竟是雪堆出来的。每常出门或上车,或一时院子里瞥见一眼,我们鬼使神差,见了他两个,不敢出气儿。……那正经大礼,自然远远的藏开,自不必说。就藏开了,自己不敢出气,是生怕这气大了,吹倒了姓林的;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
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以致鲍二家的打了兴儿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编了这些混话,越发没了捆儿。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这些混话倒像是宝玉那边的了。”其中,用“雪堆出来的”这个形象形容宝钗,从该段文字的上下文来看,尤其是“气暖了,吹化了姓薛的”,乃是比喻她如雪般的白皙柔嫩、吹弹欲破,和林黛玉的楚楚纤弱、弱不禁风,都令人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唯恐稍有损伤,犹如“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的另式说法,却更新颖传神地表达出对美丽女子的呵护崇敬之心。可见宝钗、黛玉各有其美,却都绝色无匹,堪称“天上少有,地下无双”。
不过,在钗、黛各有其美之余,若还要强分高下,则宝钗仍是略胜一筹。书中即由众人之口对钗、黛高下给予定论,如第五回道:“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脂砚斋亦夹批云:“此句定评,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第四十九回又借宝玉之口说“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从众家之评论可见,宝钗之美比起黛玉仍犹有过之,如此一来,宝钗所掣得的牡丹花签上题着“艳冠群芳”“此为群芳之冠”,便是对宝钗的如实描述。
这位少女既“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除得力于先天的健康体质与优异禀赋,更有赖于后天的教育陶冶,透过“品格端方”始能展现“举止娴雅”的优美风范。如脂砚斋所言:
瞧他写宝钗,真是又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 ,前三人(案:指宝玉、黛玉、湘云)之长并归于一身。(第二十二回批语)
事实上,当宝钗因朝廷规定而进京待选的时候,依秀女的一般年龄为计,大约是十三岁(见下文),已经是一个身心大体发展的少女;但在来到贾府之前,这位才、德、貌兼备的少女也并非凭空而生,而是经历了一段由女童到少女的成长过程与转变,在“世府千金”的身分下“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然后才有读者所熟悉的薛宝钗典型。
关于宝钗的成长过程及其转变,小说中一共有两处涉及,提供了了解宝钗的重要线索。首先,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段情节中,隐藏了宝钗成长过程的转变关键,她对黛玉说道: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
这时,林黛玉自承是十五岁,则宝钗大约是十七岁。从她的自述中可知,在七八岁之前,也是一个“够个人缠”的“淘气”女童,会做一些诸如偷看禁书的不守规矩之事。参照清末传教士泰勒·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以异国外来者的目光,对所见的中国儿童所作的描述:
那些和其他国家的孩子出生时起点是一样的中国孩子,……逐步形成一些中国孩子所特有的特点。他们会变得“淘气”,这意思是说他们有点调皮,或者说他们喜欢惹麻烦,有些难以对付。 [20]
此一说法较诸宝钗的夫子自道,简直是如出一辙,则身为这样的中国儿童之一,幼年的薛宝钗除了与其他玩伴偷看杂书,应该也会玩着当时女童们赶集、转磨、卖花、钻花瓶、找金子、猜谜之类的团体游戏 [21] ,也必然包括她长成少女之后偶尔忘情投入的扑蝶玩耍(第二十七回),构成童年淘气的具体情景。直到七八岁受到了大人严厉的管教,才回归闺秀的正轨,迄今大约十年。另外,第五十七回描述道:
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笑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 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 ?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 从实守分为主 ,不比他们才是。”
由“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之说,可见宝钗自幼也是和一般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一样浑身“富丽闲妆”,直到七八年之前才一变而为如今的“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推算起来当时大约十岁。将以上两段情节合并以观,清楚显示了宝钗的成长过程是:最早阶段乃和其他人一样的淘气女童,转变关键在于七八岁时大人正式介入的积极教育,自大约十岁以后便诞生了特属于宝钗的典型人格。而这也和宝钗服用冷香丸的年龄相当,可见作者是刻意设计安排,绝非偶然巧合,请参照下文。
不仅如此,宝钗的转变除教育力量的介入之外,让宝钗从“富丽闲妆”到“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的因素,还包括薛家的实质没落所带来的家庭危机感。所谓“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 ,以及“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 ”(第七十八回),这种没落一则是来自当家无人、经营不善,如第四回所说的:“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宝钗自己也是“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可见薛父的亡故有如支柱倾颓,是家族没落的一大关键。
再则,在清代“随代降等承袭爵位”的朝廷制度之下 [22] ,宁荣二公的国公地位世袭势必传承数代即告终绝,也确实宝玉所属的玉字辈这一代已是将面临平民化的存亡关头,财务状况更出现了重大缺口,则“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的薛家应该也步入同样的宿命轨道。由宝钗对王夫人所劝告的:
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 。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 。(第七十八回)
可见两家都是在由盛而衰的没落下趋状态,诚然是“一损皆损”的共构关系;而在此困境之下,意欲延续家业,保有世族的规模,只有转向科举一途才有可能,林如海及其家族便是可资为鉴的先例。但宝玉作为贾家“无一可以继业”之子孙中唯一的“略可望成”者,尚且面临无材补天的结果,则薛家单脉独传的薛蟠更是全无指望,身为未嫁女儿的宝钗固然心知肚明,在三从四德的社会规范之下却无能为力,只得采取一切反求诸己的消极作为,一方面“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在情感上支持母亲;另一方面则是“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以为将来预作准备,虽然杯水车薪,却用心良苦。
从前面所引述的相关文本显示,宝钗是从大约十岁开始,就已经展露此一俭朴清省的风范,衣着服饰便是最直接的外显形态。薛姨妈以母亲的贴身观察总结道:
宝丫头古怪着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七回)
脂砚斋亦指出:“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连带地,宝钗也“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得烟燎火气的”(第八回),这些恰恰都是增添女性魅力的加工品。并且宝钗不仅不喜欢外加的装饰物,连基本的必需品也都是以可用、够用为原则,绝不追新猎奇、夸富炫耀,接下来便透过宝玉的眼光,描绘出一幅勤俭的仕女肖像画:
宝玉听说,忙下了炕来至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 软帘 。宝玉掀帘一迈步进去,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 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 。(第八回)
“半旧”“半新不旧”都说明宝钗的不慕荣华,因此,当满怀内疚的薛蟠努力要讨好深受委屈的妹妹,说道:“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宝钗却加以拒绝:“连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了,又做什么? ”(第三十五回)可见她的衣箱里总躺着不见天日的新装,而那些衣裳应该都是逢年过节按礼节、依规矩裁制的; [23] 此外,宝钗不仅常穿旧衣,这些上身的旧衣也多半不是鲜艳起眼的色彩,和其他金钗们站在一起,就更显出她的低调风格: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第四十九回)
在清一色耀眼的大红对比下,李纨与宝钗两人的青色系显得暗沉许多。而宝钗的素净逼近寡妇李纨的风格,确实是始终一贯的简朴作风,也反映在个人生活空间的布置经营上。第四十回随着刘姥姥的脚步来到了蘅芜苑,所见的内部场景堪称为极简主义的实践:
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或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让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净。”
于富贵中力求洗尽铅华、素朴简净,完全符合侯门闺秀的道德涵养,正与庭院中所植的无数香花异草相呼应:包括藤萝薜荔、杜若蘅芜、茝兰清葛、紫芸青芷等等种类,都是出自《楚辞》《文选》的香草之属(第十七回),显然是刻意袭用屈原所创造的“香草美人”之文学象征传统,“香草”者,乃君子贤人之喻,带有人格之高洁与德性之芬芳的寓意。
不仅如此,如此在寒冷中绽放芳香的花草并非华而不实的浮面妆点而已,既呈现出“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而燥湿不变 ” [24] 的存在特质,还进一步展现强韧的生命意志与崇高的品格节操,在秋寒里依然青翠葳蕤、果实累累,所谓“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 ”(第四十回),意味着那独芳于萧飒中之异香远超过深山幽谷的春兰,那愈加苍翠的绿意也足以与松柏同青;而诸草同时结出的累垂果实,比诸春华秋实的“桃李红梨”以及犯寒傲霜的“橙黄橘绿”更是不遑多让。显然曹雪芹为蘅芜苑所设计的景致,乃是综合了松柏橙橘、梅兰竹菊之各种优点的总体结晶,可以说是对道德气节最全面、最高度的象征性展现,这也是此处得名为蘅芜苑的原因。由此可见,宝钗所居蘅芜苑的整个体性表现是内外一致、身心映衬,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节清操。
若进一步参照第三十七回宝钗所写《咏白海棠》一诗,作为抒情主体以主观角度的自我表白,其中以冰雪自喻其清洁贞正之心性情操,正具有个人写照的自传意义,所谓: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那“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与“欲偿白帝凭清洁”的诗句,更可见其间一以贯之的精神契合,犹如脂批所云:
全是自写身分,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纤巧流荡之词,绮靡秾艳之语,一洗皆尽,非不能也,屑而不为也。
看他清洁自厉,终不肯作一轻浮语。
好极,高情巨眼能几人哉!
恰恰呼应了第五回《红楼梦曲·终身误》中“山中高士晶莹雪”的曲文。尤其是,这种“清洁自厉 ”的精神自然外显为从实守分、甘于恬淡,不屑于讨好家长权贵,只依礼而为、不失大体的言行,故《咏白海棠》诗对“纤巧流荡之词,绮靡 秾 艳之语 ”的“屑而不为 ”,也同样表现在元妃省亲时奉命所作的应制诗上。脂砚斋便指出: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第十八回夹批)
对于薛、林二人之手笔都非颂圣之佳作,脂砚斋给了不同的解释:黛玉是能力不足,想做也做不到;宝钗则是游刃有余,却不屑为之。因此必须说,实际上真正不借机以应制诗讨好皇妃的人,是宝钗而不是黛玉,恰恰与一般读者的成见相反。
从情理逻辑而言,连可以当面讨好皇妃的应制诗,宝钗都是“有生不屑为此”,则背后所为,又更何须故作姿态?则在人物论述中常见的,将宝钗腕戴麝香串的做法视为逢迎皇妃之举,就显得不合情理;最多的是视之为希慕金玉良姻的表征,更属粗疏已极的想当然尔。
细究第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的情节所述,元妃所赐之端午节礼项目是:宝玉的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其他人的则如袭人所言:“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兹不论李纨、凤姐等年轻媳妇另有安排,府中人是依伦理辈分而有等差之别,可列表如下以观之:
从这个表格中,清楚可见伦理辈分是最重要的依据,至于玉字辈的同一代中又区分出差异,则是以“家族继承人”的身分作为标准,众姊妹将来必属他姓,则宝钗之与宝玉同级,便等于是“宝二奶奶”的指派。无怪乎宝玉疑惑道:“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而敏感的黛玉更领略到其中深意,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于是又掀起二玉之间的一段风波。
其中,黛玉被降为姊妹等级,而宝钗被提升为宝玉一级的差序旨意固然十分明确,但考察两个等级的异同,二宝所多出者乃是“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其余与众姐妹相同者则是“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此即袭人所说“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的意思。可见宝钗左腕上所笼戴的红麝串子并不是用以区隔钗、黛之别的重要物件,反而正是等同彼此的共同品项所在。如此一来,将宝钗之笼戴红麝串视为希慕金玉良姻的表示,便是缺乏证据力的说法。
既然迥非承蒙钦点之沾沾心理的外显,而宝钗本性又是如此之不慕容饰,所谓“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第七回),日常生活中也“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第五十七回),则其所以特意笼戴红麝串的原因,便只是对贵妃赐礼的一种礼貌性表示。正如对元妃无甚新奇的灯谜诗,宝钗会刻意做出“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第二十二回)的反应,这对尊重君臣之伦、谨守人际仪节的性格而言,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表现。
至于宝钗颈挂金项圈的道理亦有异曲同工之处。金项圈是癞头和尚“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第八回),脂砚斋就此说道:
一句骂死天下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妖粉怪。(第八回批语)
既感无趣,却又依嘱佩挂身上,乃因癞头和尚所给的冷香丸,是唯一能对其群医束手无策的无名喘嗽之症生效的“海上方”,既已确实展示了神通妙验之超凡能力,其所给予的“两句吉利话儿”也因之获得某种权威性,让薛宝钗在感到“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之余,愿意对其“叫天天带着”的嘱咐奉行如仪。则红麝串、金项圈的佩戴,都从文本中获得了比追求金玉良姻更合理的解释,亦足以提供《临江仙》一词非关攀附的佐证,请见下文。
必须说,宝钗的成长与转变,反映了“受得富贵,耐得贫贱”(第一百○八回)的人品性情,显示出“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底蕴。其可贵处一如明代洪应明《菜根谭》所言:
淡泊之守,须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不然,操守未定,应用未圆,恐一临机登坛,而上品禅师,又成一下品俗士矣。 [25]
就此,已经和贾母深体时艰,主动省俭用度,实是如出一辙。如第四十七回贾母说道:“凡百事情,我如今都自己减了 。”又第七十五回贾母也提醒大家“上几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这些蠲了罢,你们还不听。如今比不得在先辐辏的时光了。 ”这些足证宝钗是一个足以承担家族命脉的“准母神”,是贾母之后的隔代继承人,成为家族败落后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