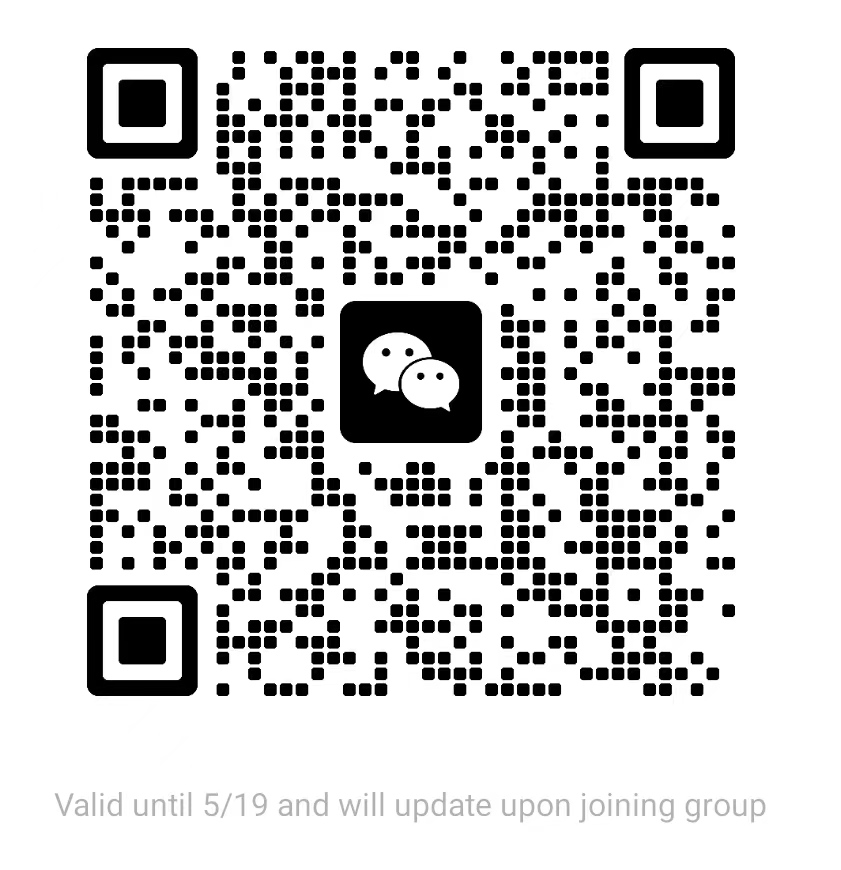- 读书 >
- 大观红楼:欧丽娟讲红楼梦 >
- 第三册 >
- 第五章 薛宝钗论
七、相关诗词的寓意重估
在古典文化中成长的小说家,诗词就和经学、子学一样,都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知识,其娴熟自是必然,也往往运用于小说中,成为中国小说的一大特征。《红楼梦》是将韵、散结合得最成功的一部小说,叙事与诗词有机地融合为一,互相加强也彼此烘托,人物的形象也更加鲜明。不过,诗词虽然属于小说的血肉之一,其功能与意义从属于小说内容而定,但其创作方式却也自有悠久的诗学传统,无论是典故、修辞、用语、句法与寓意等,都应该以传统诗学的角度来把握,尤其是直接引述的唐宋诗句,更必须回到原诗以及诗史的脉络才能正确诠释,不致望文生义而曲解小说家引述的用意。这是对古典诗学知识陌生已极的现代读者所最需要强化的地方之一。
(一)“任是无情也动人”释义
首先,如果纯以小说情节的描述以观之,宝钗所掣得的“任是无情也动人”这句花签诗本身实不应带有任何负面的意涵,才合乎曹雪芹特有的创作手法,并切中一般的人情世理。
就曹雪芹书写此回的创作手法而言,乃是用“冰山一角”式的引诗策略,摘取传统诗词中的吉祥佳语,以配合当时寿庆的欢乐气氛;却将人物之悲惨命运暗藏于未引之诗句中,以达到“谶”的作用。因此群芳诸艳所抽中的每一支签词,包括探春的“日边红杏倚云栽”、李纨的“竹篱茅舍自甘心”、湘云的“只恐夜深花睡去”、香菱的“连理枝头花正开”、袭人的“桃红又是一年春”等等,莫不是浮露在阳光之下的冰山顶层,充满希望、明朗、满足甚至幸福洋溢的正面意涵;即使林黛玉的“莫怨东风当自嗟”一句以“怨”“嗟”字堂堂出现,但身为签主的黛玉却是报以“也自笑了”的反应,显然心意颇为悦服肯定。至于麝月的“开到荼䕷花事了”一句虽因稍带不祥之意,令宝玉看后“愁眉忙把签藏了”,其字面却也依然带有含蓄蕴藉的美感,且未曾涉及任何意义的人格批判,仅仅是自然界生命规律的客观反映。既然“美好”“含蓄”而“不涉及人格批判”乃是所有花签诗的共同基调,宝钗的签词理当不可独独例外,若直接认取其中的“无情”二字即断定为宝钗性格的判词,其尖刻率露无论如何都与“美好含蓄”的原则背道而驰,曹雪芹如何能有如此之败笔?
再就一般的人情世理而言,书中描写宝钗于群芳之中首先掣得的这支签,不但签上于签诗下注云:
“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侑酒。”众人看了,都笑说:“巧的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
而且接下来的情节是: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掷与宝钗。(第六十三回)
如果说这句签诗有丝毫的贬损之意,则那“群芳之冠”的注解、在场众人的笑认共贺,以及宝玉一见之下更是到了神魂颠倒的忘情地步,不断喃喃诵念,都会变成十分矛盾的反应。换句话说,若依照直接以字面上之“无情”为判词的论证法,则将会得出曹雪芹认为“无情”者亦足以为诸钗冠冕,而众人皆以“无情”为值得庆贺,且宝玉竟会为“无情”神魂颠倒的推理结果!这岂非匪夷所思?更何况,连贾政都能对诗词语句有足够的敏感与认识能力,因此对诸钗所做“不祥”的灯谜诗感到烦闷悲戚、伤悲感慨,回房后翻来覆去竟难成寐(第二十二回),则相较之下更为冰雪聪明、玲珑剔透的贾宝玉等人,竟然都不能察觉签诗中明白坦露的“无情”之意,而相与共贺、赏爱忘情,这当然是不合逻辑的说法。
由此已经足以显示,“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一诗句不但绝没有现代所以为的“无情”之意,恐怕还恰恰相反。
1.语法学的正确解析
更重要的是,诗句本身之意旨究竟如何,理当还原于全诗整体之语序意脉始得以确切定位;而从语法的结构分析、律诗的对仗法则等范畴来看,出自晚唐罗隐《牡丹花》诗的此一诗句其实并没有“无情”的意涵。全诗云: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从律诗对仗的规则来看,“任是无情也动人”与上句之“若教解语应倾国”乃是彼此对偶的完整一联。依照语法学或修辞学的分类,这两句都不是一般的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描写句(descriptive sentence)或判断句(determinative sentence),也就是它们在构句形式上并不是叙述行为或事件,而其语意内涵并不是对某一现象、状况或事物属性的描写,更没有断定所指事物属于某种性质或种类,因为两句之结构都属于句中包含两个句子形式的“复合句”(composite sentence),各以“若教”和“任是”等语词形成前分句,然后再以“应”“也”等联词所领起的后分句加以构组而成。更精确地说,两句都属于“假设复句”,而在假设复句中前分句所指涉之意涵,都是非事实性的存在。以“若教解语应倾国”来说,“若教解语”乃是提出假设的一个分句,而“应倾国”则是另一个分句,说明在前述假设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 [87]
至于对仗的“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任是”一词是“纵使是”“即使是”的意思,而“任是……也……”的句型,则明白属于假设复句中的“让步句”,其中的前分句有退一步着想的意味,亦即先承认某种假设的情况,后分句却从不同或相反的方面做出结论; [88] 换句话说,前分句(即“任是无情”)表示让步,即姑且承认某种既成事实或某种假设情况,后分句(“也动人”)表示转折或反问,指出后事并不因前事而不成立。 [89] 则这种让步句属于“转折类复句”中的一类,意指“分句间有先让后转关系的复句” [90] ,而由虚拟的假设构成的前分句称为“虚让”,“虚让是对虚拟情况的让步,或者是带虚拟口气的让步,……是故意从相反的方向借p事来托出q事,强调q事不受p事的影响。不同的是:实让的p一定指事实;虚让的p一般是假设,不是假设的也带上一定的虚拟口气”。 [91]
从上述修辞学的说明可知,就句法结构而言,“任是”一词都是表示虚拟的标志,是“故意从相反的方向”对“虚拟情况”所做的让步表示。如此一来,“任是无情也动人”不仅确实没有无情之意,并且其真正的重点是在于“动人”上,配合另一段脂批,便可以看得更清楚。针对第一回中绛珠、神瑛建立木石情盟之描写,脂砚斋眉批云:
古人之“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此之谓耶?
其中所引的诗句,出自唐代刘长卿《戏赠干越尼子歌》:“一花一竹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全唐诗》卷151)恰恰可以与“任是无情也动人”互为平行类比。作为对“尼子”的戏赠之诗,刘长卿乃是夸言此一六根清净之女尼依然保有颠倒众生的魅力,连“无情”都能动人至此,更哪堪有情?这可以说是对倾国美人的绝大赞美,也才是宝钗获得“群芳之冠”,在场众人也都笑认共贺而宝玉更为之颠倒忘情的原因。
2.“无情”的另一含义
更发人深省的是,即使脱离了假设复句中虚拟让步句的修辞脉络,单单只就“无情”一词而言,也未必只有通俗常识下的负面意义。事实上,在传统思想文化中,“无情”甚至还是一个至高的、正面的哲学用语,是圣人的无上境界。
在主情、唯情的浪漫思维里,“情”是生命存在的根本价值,甚至是存在的理由,所谓:“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 [92] 到了现代,“情”已经变成一个单单只要出现这个字眼就具有强大魅惑力的概念,“无情”自然也就沦为否定价值的负面语。但其实从人格修养、宗教修炼的角度,情却反倒是一种障碍,是必须克制转化的难关。由于“情”是一种主观感受的发用,容易受到主体的局限而不免偏私的性质,因此欲超乎情的偏私局限者,即必须否定“情”的主观执一性,这便是一种对“无情”的诠释。如宋代理学家程颢曾指出: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93]
其中所谓的“无情”,正来自于一种不限定、不执着而顺应大公、普施万物的廓然表现,以之衡诸宝钗处世时,所谓:
待人接物,不疎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第二十一回脂批)
此一表现岂非与之丝丝入扣?一旦泯除主观执着,超脱亲疏远近的情感差序格局,便能不偏不倚地权衡裁量,而事事归诸天钧与公道,并达到随运任化的自在境地。在此一人生态度之下,非独人际之间亲疏远近的情感差序可以一视同仁,连个人遭遇之炎凉甘苦、天地万物之聚散生灭都可以夷然自安不受影响,如此一来,便达到庄子所说的境界:
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94]
这不仅符合脂砚斋对冷香丸之命名所阐释的意义:“历看炎凉,知看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同时也呼应了第七十回薛宝钗所填《临江仙·咏柳絮》中,透过“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两句而展现的豁达稳定。如此种种,皆合乎程颢所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无情说。
(二)《临江仙·咏柳絮》释义
第七十回薛宝钗所填《临江仙·咏柳絮》一阕,在历来习惯“钗、黛对立”的成见下,往往被误以为是其个人热切追求现实价值的展现,并且是与黛玉针锋相对而作。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文本的基本描述,属于成见所致的穿凿附会,更忽略了其中所具有的两个范畴的积极意义,未免买椟还珠。
试观当时的完整情况是:在诗社重开后的填词活动中,当限定的时间一到,探春率先写出只做半首的《南柯子》,却触发了交白卷的宝玉灵感泉涌而续成后半,写道是: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
众人笑道:“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纵然好,也不算得。”说着,看黛玉的《唐多令》: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是《西江月》: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
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调壮。‘几处’‘谁家’两句最妙。”然后才是宝钗的压轴之作:
宝钗笑道:“终不免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众人笑道:“不要太谦。我们且赏鉴,自然是好的。”因看这一首《临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
湘云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底下道:
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气力,自然是这首为尊。缠绵悲戚,让潇湘妃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
很明显地,宝钗之词是紧接在宝琴之后,所谓“终不免过于丧败”是对前面所有作品之共同特性的评论,根本不是针对黛玉而来;若说有针对性,所针对的也是大观园诗词中普遍存在的离散主调与伤悼哀音。
最关键的是,这种不同调并非来自于美学上或生命情调上的龃龉互斥,而其实带有积极性的正面努力。其一,是诗学上创新或突破的“翻案”表现。
1.美学的创新与突破:翻案策略
《红楼梦》中使用翻案法的具体操作共有三处,主要是透过薛宝钗来发挥展现。第六十四回记载宝钗赞赏林黛玉之《五美吟》时,所陈述的意见即是翻案的本质,宝钗说道:
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此处薛宝钗是以读者和诗评家的立场赞美他人的诗歌作品,以为“善翻古人之意”乃是作诗的第一义,而“各出己见,不与人同”“命意新奇,别开生面”即是诗歌透过翻案所能达到的最高价值。这是书中对翻案手法的初次展露。后来填写《柳絮词》时,薛宝钗更抱着与众不同的创作心态而亲自以作品为翻案法作了实践,从而充分显现她自己的确是翻案技法的知音解人。
针对一般人容易因为柳絮轻薄无根无绊的特性而附加漂泊零落的悲剧感受,宝钗特意以“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为创作原则,即是出自刻意求新立异的翻案手法,可以促使作品在众口一腔、千篇一律的俗套中脱颖而出,达到新颖独特之效果,完全呼应了宝钗自己先前赞美林黛玉《五美吟》时所谓“各出己见,不与人同”“命意新奇,别开生面”的说法。如此一来,词中一方面以反诘语气,对主流成见提出“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的质疑,也是对柳絮(以及众女儿)顺任那飘泊零落之宿命持以一种保留态度;另一方面更写出“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这积极的阳光意志,如是种种,都展示了不落熟套的最佳典范。于是乃如宋代严有翼所言:
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 [95]
这便清楚指出薛宝钗这首《临江仙·咏柳絮》之所以赢得众人之喝采,并拔得头筹的原因。就全书之艺术设计而言,也更增加了衬托悲凉之调的对比因素,完成艺术上、思想上“二元对立”的形式特征与均衡的结构性。
但技巧只是表面的。在《红楼梦》整体的艺术氛围之中,运用翻案法所蕴藏的更深的意义,都不只是一般文人逞才竞技的心理展示而已,更深层的是反映出一种试图驱散大观园中弥漫的“悲凉之雾”的努力,是诗谶观(一种以诗为预言的信念)在同一个本质上进行逆向操作的运用成果。这便是宝钗《临江仙》之所以不同调的第二个积极的意义。
2.命运的翻转与改善:翻案目的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评论里,一直存有一种“诗/运”一体、以诗观运的诗谶观,《红楼梦》亦然,所谓“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 [96] ,即是对诗歌渗透命运、甚至指引命运之魔力的最佳阐释。
第七十六回记载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时,当黛玉、湘云联诗至于“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这一联警句之际,不但湘云对黛玉所对之“葬花魂”既赞且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作此过于清奇诡谲之语。”语中已颇有诗谶的警觉;接着妙玉更及时现身打断,原因就是“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而有,所以我出来止住”,接着所作的续诗也不只是帮忙收尾,而是“依我必须如此,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在在可见诗歌影响乃至决定命运的思维。
同样地,当第七十回林黛玉作出凄美欲绝的《桃花行》后,宝玉一见便堕下泪来,立刻断定是“潇湘子稿”,宝琴戏谑地笑诌是她的手笔,宝玉便道:
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所以不信。……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可见诗歌的创作风格不只是关乎才能,还隐含了命运的反映、暗示乃至指引,因此爱护堂妹的宝钗便“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唯恐损及其气数而致不幸。由此可见,宝钗不仅是爱护自己人而已,她把这种关心与努力扩及园中诸钗,对前面那些“终不免过于丧败”的作品扭转乾坤,与妙玉的“依我必须如此,方翻转过来。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第七十六回)如出一辙。可见“翻转”的做法已然有如破解悲剧的法门,利用诗歌攸关气数、影响命运的神奇作用,反过来借助清明朗健的诗歌以扭转颓败凄楚的人生。
换言之,诗歌既然乃是“亦关人之气数而有”的一种象征符码或命运载体,具有支配命运的神奇力量,而“支配”也者,又有祸福吉凶正反相异的不同结果,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神奇又神秘的力量可以导向毁灭和地狱,也可以通往创造与天堂。于是,当已经出现“过于颓败凄楚”的诗句,奏出了悲剧的前奏或序曲,便必须在预言落实之前适时加以遏止,否则宿命的悲剧便毫无改变的余地;而欲“止住”预言成为事实,其唯一的做法便是翻案,因此妙玉之续诗便是将诗作前头的凄楚之句“翻转过来”,如此便无甚大碍,同样地,宝钗在一片“过于丧败”的哀吟声中,将特属于柳絮的“无根无绊”的栖惶茫然,转化为一种飘扬自由、凭风向上的追求人生的积极意志,也是一种将悲戚伤悼之气数加以翻转的表现。
清吴景旭曾引严有翼《艺苑雌黄》所言来解释翻案技法,指出:
牧之数诗(案:指《赤壁》《题商山四皓庙一绝》《题乌江亭》等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迭山所谓“死中求活”也。 [97]
此说以“反其意而用之”解释翻案的思维模式,以“死中求活”来解释翻案法的运用效果,也适用于《红楼梦》中,诸人在重重围困之宿命悲剧中力图突破的意志:大观园中“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98] ,弥漫着一种由月冷、花残、香消、春去、柳飞甚至泪血、人亡的哀凄,宝钗“偏要把他说好了”的《临江仙》,则是借由翻案法特有的“反其意而用之”的操作模式,对诗谶所模塑的悲剧命运进行逆向推演,展露的正是一种“死中求活”,以阳光驱散遍布四周之悲雾的积极与乐观。此一“死中求活”的挣扎虽不能真正使众金钗的人生得以绝处逢生、反缺为圆,却为《红楼梦》那弥天盖地的悲剧意识平添几许庄严宏伟的英雄气息,那奋力挣扎、贲张不屈的努力,更令人油然泛起崇敬之意;而众人评赞宝钗此篇《咏柳絮》时拍案叫绝,一致公认“果然翻得好力气,自然是这首为尊”并大声喝彩,更毋宁可以视之为对悲雾中乍现之阳光所抱持的高度肯定。 [99]
3.“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来历与用意
关于篇末的“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二句,学者大多认为与宋代侯蒙的《临江仙·咏风筝》有关,所谓:“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并据以推论薛宝钗攀慕荣华富贵、献媚当权人士、冀求飞黄腾达之世俗性格。 [100] 此种说法已几乎成为主流之定调,且此种见解又常常与薛宝钗“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第七回)相联系,并将此一性格具体化于对金玉良姻之热切追求,成为薛宝钗论述中演绎出种种阴谋嫁祸说的基点。
对此一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合理性而言,不乏极少数学者提出怀疑,如同样在承认此阕词与侯蒙《临江仙·咏风筝》的渊源关系之下,毕华珠的推论即迥然不同,认为历来红学家把“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说成是成就“金玉良姻”的象征,乃是牵强附会之论,因为“金玉姻缘”在大观园中常常提起,薛宝钗也早已心中有数(见第八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四回);何况金玉姻缘乃是四大家族内部联姻,中表成亲,门当户对,根本谈不上高攀;再说凭薛宝钗的门第财势、人品才貌,即使金娃不配玉郎也不失为其他王孙公子的夫人,所以金玉姻缘在薛宝钗心目中不可能是“送我上青云”的凭借。因而此阕词与《螃蟹咏》一样,都属于绝妙的讽刺词,也都是曹雪芹借题发挥,寄托其伤时骂世之感慨。 [101]
此一说法回归于小说所蕴涵的社会基础,把握到人情世理上的客观性,提供了比富贵说更可靠的说服力。只是此说虽然足以推翻富贵说,但以伤时骂世的讽刺寄托为论,却恐怕不易成立,毕竟与寓意明白可验之《螃蟹咏》相比,这阕《临江仙》以“我”为与柳絮相互定义的第一人称,全篇又充满对生命展望的明朗氛围,都与伤时骂世的讽刺意味相距甚远。因此,从词句之取资渊源、写作之意匠用心都有再加厘清的空间。
其次,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坐实宝钗热中权贵的罪名,还包括选秀女。但这也是对历史无知却想当然尔的成见。所谓“选秀女”,是一种为皇室后宫提供年轻女性,作为指婚对象(妃嫔)和服务人员(宫女)的选拔制度。清代所选的秀女都是来自旗人,“八旗所有官员兵丁乃至闲散之女,须一律参加阅选,如未经阅选便私行聘嫁,该管各官上自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本人父母族长,都要治罪” [102] 。而随着外八旗与内三旗的两个不同系统,清代的选秀女制度也分成两种管道,按《国朝宫史》所言:
凡三年一次引选八旗秀女,由户部奏请日期。届日,于神武门外豫备,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关防,以次引看毕,引出。……
凡一年一次引选内务府所属秀女,届期,由总管内务府奏请日期,奉旨后,知会宫殿监。宫殿监奏请引看之例同。 [103]
明确可见两者分属不同的系统,彼此互不相干。然而,除阅选的频率不同外,两个管道所选出的秀女也有不同的用途,这才是最大的差别,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八旗满、蒙、汉军正身女子,年满十三岁至十七岁者,每三年一次参见验选,选中者,入宫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验选前,不准私相聘嫁。
其二,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亦选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可见,同样是选‘秀女’,八旗女子和内务府女子中选后的境遇却大相径庭。内务府女子被选入宫,多充当杂役,满二十五岁才能遣派出宫。 [104] 为皇室无偿服役十余年,按当时标准,出宫时已是十足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谈何容易?内务府女子不乐入选,乃人之常情。” [105]
从这两种差别来说,元春的“选入宫作女史”,并不是八旗系统的为皇帝嫔妃或备王公贵族指婚之选,再参照宝钗的情况就更清楚了,第四回写到薛家“现领内府帑银行商”,显示与内务府关系密切,且宝钗之所以来到贾府,便是因为:
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 ,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
这段话可以说是元春入宫的进一步补充,可见元春与宝钗的入宫是在“聘选妃嫔外”的另一个不同的管道与功能,属于内务府包衣三旗的选秀女系统,并不是作为皇子王公的指婚,而较偏向宫女性质。如此一来,元春封妃的际遇可能是历史记录中,由内务府三旗所选出的秀女晋升为妃嫔的少数例子,如学者所指出:“有清一代,内务府三旗女子通过选‘秀女’晋身嫔妃者代不乏人,其母家一跃而为皇室戚畹,父兄子弟多跻身枢要。” [106] 也可能是融合了外八旗与内三旗这两种管道的虚构,无论何者,都说明那是非常态的罕见特例,并非人力所能争取。
尤其是,所谓的“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清楚指出这是所有相关家庭都必须遵守的义务,违逆不得,并非个人意志所能选择决定,则宝钗的入京待选只不过是遵行朝廷规定的义务而已,最多也是“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如何能说是存有追求飞黄腾达的雄心壮志?何况,这段情节乃是清代八旗制度下“选秀女”的反映,被用来作为宝钗来到贾府以发展叙事的方便法门,尔后完全没有再加以延续,也一无追求飞黄腾达的迹象,如何能坐实为论?足证读者应该先了解基本历史知识,以免以今律古,错失正确理解人物的性格真髓。
此外,关于“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两句的出处,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比宋代侯蒙《临江仙·咏风筝》更早的诗歌源头,即中唐李贺的《春怀引》,其诗云:
芳蹊密影成花洞,柳结浓烟花带重。……阿侯系锦觅周郎,凭仗东风好相送。(《全唐诗》卷394)
以曹雪芹不断被友辈敦诚类比于李贺,所谓:“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牛鬼遗文悲李贺”“诗追李昌谷” [107] ,对李贺诗的熟稔自毋庸置疑,篇中所谓“凭仗东风好相送”,乃以东风为攀升传远的媒介,以“好相送”解释风中飘飞的行动意涵,一反零落无依的悲感而充满温馨、期待的正面情致,将向下飘零沉坠的沦落颓靡转而为向上昂扬提升的攀高追寻,正是薛宝钗在众人一片丧败之音中,力求翻转而写出“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脱胎之处。而从整体来看,《春怀引》的秾丽缠绵与宝钗《临江仙·咏柳絮》的潇洒豁达虽有调性之别,却都是歌咏柳絮,也同样具备了诗情画意,迥异于侯蒙《临江仙·咏风筝》的平板刻露、尖直外显而有失含蓄,应该才是宝钗《临江仙》真正的血脉所自。 [108]
更应该指出的是,风吹柳絮所送之“青云”,并不必然就是富贵荣达的同义词,在古典文献中其含义之丰富多元,可以指:青色的云、高空的云(亦借指高空)、高官显爵、远大的抱负和志向、隐居,甚至比喻黑发 [109] ,必须视情况而定。从这些用法中,已可见同一个词汇竟可以用在截然相反的地方,连类所及,由之延伸组构的“青云士”“青云客”“青云梯”等词语,也都各自产生了两种对立的用法,诸如:南朝山水大家谢灵运曾有“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之乐与“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之叹 [110] ,唐诗中则有高适《同颜六少府旅宦秋中之作》的“逸气旧来凌燕雀,高才何得混妍媸。迹留黄绶人多叹,心在青云世莫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杜甫《北征》的“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与《寄从孙崇简》的“牧竖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等,都与贵显荣达无关;而“青云梯”一语,虽可以比喻谋取高位的途径,但于上述诗句中却是指高峻入云的山路,引申为高蹈出世乃至羽化登仙的象征,在在指向一种超脱浊世纷扰而飘然世外之逍遥清畅的境界。由此可见,“青云”一词的意义完全要依上下文而定,清末评点家王希廉便认为:“‘青云’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云羡鸟飞’句,后人遂以讹承讹,作为功名字面。宝钗词内‘青云’字,应仍作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映照。” [111] 现代人直觉地以自己唯一熟悉的高官显要加以解释,未免张冠李戴之误。
回到宝钗的《临江仙》仔细重读,首两句的“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就已经将柳絮的空间位置给予正面定调,以至于湘云率先赞美:“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接着“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更是以反诘语气抗阻沉沦坠落的向度,再透过“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的坚定稳住此一人间高度,为进一步的超越提供良好的基点,与“历看炎凉,知看甘苦,虽离别亦能自安 ”(第七回脂批)的贞定之心一以贯之,甚至带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12] 的屹立不拔;最后便是“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向上飞升,反向改变了飘随逝水、委堕芳尘的下坠命运。由此显示“青云”是挣脱尘俗牵缠、超越地心引力的天空至高点,恰恰对立于“随逝水”“委芳尘”之匍伏纠葛,兼具了诗学上、命运上大胆的双重突破,因此才能胜过黛玉的缠绵悲戚与湘云的情致妩媚而夺魁。
这也提醒我们,任何文句都属于整体作品的一部分,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才能取得正确的定位。一般将“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两句单独割裂出来加以扩张解释的解读法,忽略所属整阕词、整段情节的完整脉络,正是标准的断章取义,值得商榷。